北京-莫斯科-華沙-柏林-布拉格-布達(dá)佩斯-貝爾格萊德-地拉那-貝爾法斯特-巴黎-倫敦:英特納雄耐爾���。這條旅行線���,是為了讓這些總是風(fēng)云激蕩的城市帶給一個旅人尋找和憑吊的歷史感,那是一個紅色的時代�����,一種高蹈的理想實驗����。
陳丹燕�,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上海作家協(xié)會理事���。她的作品形成了一種非常有風(fēng)格的旅行文學(xué)����,主要作品有《上海的風(fēng)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等。
★這里是自由的柏林
蝴蝶的翅膀
荒謬的幸福感
自由柏林的咖啡館
生長在室內(nèi)的榕樹
芭芭拉記
常青
維尼塔站
男人們
一種令人惆悵的陽光
舊氣
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們
偶爾留下的照片
查理檢查站
★ 微黃的昏暗
《嘿�����,裘德》
頹敗但直指人心的美
俄羅斯的糖霜
俄德翻譯者
桃紅色
口琴
微黃的昏暗
一道藍(lán)邊
早餐
一個女孩清澈的說話聲
七十年代的攝影冊
白云
澳大利亞草
★ 蚍蜉死在大樹下
……
一個女孩清澈的說話聲
我是乘坐黃昏時最后一班火車來到克魯姆洛夫的���。韋伯說要是火車出問題����,不得不晚到�����,那么到了以后就給他電話�,他好過來給我開門。這已經(jīng)是二○○九年捷克的秋天�����,我在網(wǎng)上預(yù)訂了克魯姆洛夫老城里的家庭旅館����,韋伯家開的�����。
穿過波希米亞森林的支線小火車開開停停����,一車子的人安然若素�,坐在我對面窗邊的男人滿臉都落在金燦燦的陽光里,亞麻色的眉毛和灰色的眼珠好像褪盡了顏色似的����,惹人多看兩眼。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害怕到得晚了�,今晚真沒住處。但是波希米亞的森林在蜿蜒的丘陵上起伏�,夕陽下大群黑色的鳥在林梢揚起又落下,顯得森林有點憂郁��,十分好看��。我少年時代沉迷在舊歐洲小說和交響樂里的日子��,又開始在心里的什么角落中蠢蠢欲動了���。
只要在歐洲旅行�,就總是會迎來這樣的時刻��,從心中的軌道����,一路滑翔入自己的少年時代,那是寒冷的上海��,天光總是暗淡��,但心中總是飛翔著輕盈而絕望的夢想�����。
我還是順利到了韋伯家的小旅店����,巴洛克時代方方正正的老房子,在老城背靜的街里�����,屋頂上蓋著最后一抹金燦燦的夕陽。
我這房間小小的��,床上有股洗衣液的檸檬添加劑氣味���。這氣味讓我想起從前慕尼黑我住過的那個安靜的坡頂房間��,床也靠在暖氣片旁邊放著�,一張小沙發(fā)床��。也是白色泡泡紗的被罩��,也有一股令人安心的德國洗衣液氣味�����。那是我第一次客居在歐洲的一戶人家��。要是從飛機上看�,就好像一粒米落在米缸里那樣日常。
我把自己行李里的計算機拿出來����,接上電源,播放自己選好的音樂��,林昭亮拉的莫扎特,我從來喜歡的曲子和小提琴演奏者����,他在唱片封面上的照片�,也是一路慢慢沒了嬰兒肥,生出白發(fā)和皺紋�����,但是與莫扎特一樣沒有風(fēng)霜����。
然后,找出來幾個紅艷艷的蘋果�,它們就好像白雪公主后媽給她的毒蘋果那么好看。我在慕尼黑火車站等車的那個清晨買的���,一直都沒吃���,可一路都拿出來放在旅館房間的桌上,好像這樣布置一下��,就能讓那些陌生的房間因此變得熟悉�。
小狗出去散步,不也會一路走,一路撒尿��,而且一路聞著找著����,與我的林昭亮和蘋果一樣。
安靜的街巷里傳來一個女孩子清澈的說話聲����,捷克語,聽不懂�。但是懂得那里面東歐沉重的大舌音帶來的浪漫與粗重交織的語言氣氛。
對面的房子突然一振���,好像一張平靜的臉上突然挑起了眉毛�,那是亮了一盞燈���。
燈光透過厚重的白色蕾絲窗幔�,這里真的是波希米亞森林中的老城哎�����,白線勾起來的蕾絲顯得有點憂郁�����。燈底下是誰?我見到窗邊的外墻上保留了一幀古老的濕壁畫���,方方正正的��,畫著穿了大花裙子的圣母�����,抱著她的孩子。這就是宗教戰(zhàn)爭時代落下來的印記吧����。
我拿了錢包出去吃飯,一邊決定要喝點酒���,即使是一個人旅行����。
老城安靜極了���,過了一座橋����,聽見伏爾塔瓦河在暮色中響亮地流過,打著旋����,嘩嘩地撞在河中央的石頭小丘上。想起聽過的《伏爾塔瓦河》的合唱曲���,少年合唱團唱的���,“在我的祖國波希米亞群山中,有兩條美麗清泉奔流悠長�,一條溫和一條清涼匯流成河”,心中希望自己見到的�����,就是那森林中清泉剛剛匯集流出的河流�����。這時候突然想起����,我有個朋友一輩子都喜歡《伏爾塔瓦河》這曲子��,他死了����,葬禮上用的曲子也是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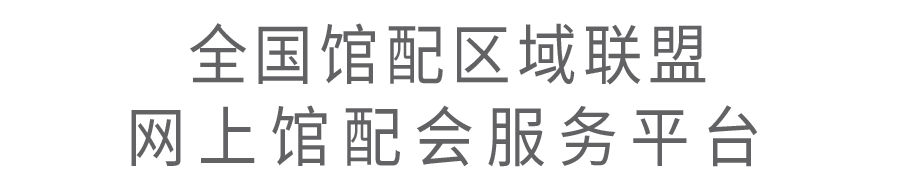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書單推薦
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
新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