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燾文選》收錄了林燾先生的17篇論文���,時間跨度為1955~1995年。所選論文基本涵蓋了林燾先生所涉獵的學術領域���,按照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編排�,分別是:一��、漢語規(guī)范化研究(2篇);二�����、北京話研究(7篇)����;三��、語音與語義���、句法關系的研究(2篇)���;四、實驗語音學研究(3篇)����;五、漢語史研究(3篇)���。
隨著時光流逝���,前輩們漸行漸遠�����,其足跡本該日漸模糊才是�����;可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有心人的不斷追憶與闡釋��,加上學術史眼光的燭照��,那些上下求索���、堅定前行的身影與足跡���,不但沒有泯滅,反而變得日漸清晰���。 《北大中文文庫》是北京大學出版社新推出一部叢書�,書中選擇了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zhèn)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掀���、徐通鏘���、金開誠、褚斌杰)���,為其編纂適合于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
隨著時光流逝,前輩們漸行漸遠����,其足跡本該日漸模糊才是;可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有心人的不斷追憶與闡釋����,加上學術史眼光的燭照,那些上下求索��、堅定前行的身影與足跡����,不但沒有泯滅,反而變得日漸清晰��。
為什么���?道理很簡單��,距離太近�,難辨清濁與高低��;大風揚塵���,剩下來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躍在舞臺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還能常被學界記憶,很難說�����。作為讀者�,或許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視線���;或許觀察角度不對�,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魯迅的話��,“偉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學界紛紛傳誦王國維����、陳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時間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總會有剝落的時候,那時��,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為學術史上的“關鍵時刻”�,方才一目了然�����。
當然�����,這里有個前提�����,那就是���,對于那些曾經(jīng)作出若干貢獻的先行者���,后人須保有足夠的敬意與同情。十五年前����,我寫《與學者結緣》,提及“并非每個文人都經(jīng)得起‘閱讀’�,學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覓到一本絕妙好書的同時�����,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學者���,實在是一種幸運”�。所謂“結緣”,除了討論學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來��,與第一流學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結緣”��,是一種提高自己趣味與境界的“捷徑”����。舉例來說,從事現(xiàn)代文學或現(xiàn)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與魯迅“結緣”��,就因其有助于心靈的凈化與精神的提升��。
對于學生來說��,與第一流學者的“結緣”是在課堂����。他們直接面對���、且日后追懷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無味的“課程表”����,而是曾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們——20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此時此地的“小環(huán)境”���,講授者個人的學識與才情�,與作為聽眾的學生們共同釀造了諸多充滿靈氣�����、變化莫測�����、讓后世讀者追懷不已的“文學課堂”��。
林燾(1921~2006)����,字左田����,生于北京�,福建長樂人。著名語言學家���,在社會語言學����、漢語語音學�����、漢語音韻學���、對外漢語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xiàn)代語音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事業(yè)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他為北京大學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代表作有《林燾語言學論文集》、《語音學教程》和《聲韻學》等����。
那些日漸清晰的足跡(代序)
前言
關于漢語規(guī)范化問題
現(xiàn)代漢語詞匯規(guī)范問題
北京話的連讀音變
北京話兒化韻個人讀音差異問題
北京話去聲連讀變調新探
北京東郊陰陽平調值的轉化
北京話兒化韻的語音分歧
北京官話溯源
北京官話區(qū)的劃分
現(xiàn)代漢語補語輕音現(xiàn)象反映的語法和語義問題
現(xiàn)代漢語輕音和句法結構的關系
探討北京話輕音性質的初步實驗
聲調感知問題
京劇韻白聲調初析
陸德明的《經(jīng)典釋文》
“人派三聲”補釋
日母音值考
林燾先生學術生平
林燾先生著作一覽
把以上各種來源的移民計算在一起��,從明代開國到遷都北京��,五十多年的時間�����,全國各地先后移居北京的漢族人每戶如以五口計����,估計當有幾十萬人。這些人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內和附近各地�����,大大改變了北京的人口結構�����,使得明初人口十分稀少的北京再度繁榮起來��。這時和北京話接觸最頻繁的已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數(shù)民族語言�����,而是來自中原和長江以南的各地漢語方言了��。
方言之間雖有分歧��,但同是漢語�����,差別不大���,這可能是中古以后發(fā)展迅速的北京話到明代趨于穩(wěn)定的主要原因�����,當時方言來源不一���,五方雜處,也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區(qū)的方言靠攏���,自然���,在明代這二百多年中��,北京話不可能毫無發(fā)展�����,在發(fā)展過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所接觸的各地方言的影響���。明沈榜《宛署雜記》第17卷“方言”條下說“第民雜五方��,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可見明萬歷年問(1573-1620年)北京話詞語來源就已相當復雜��。沈榜共收集當時北京方言詞語八十余條�,流傳至今的只有一半左右,其余有的來自外族語(如“不明白日烏盧班”)�,有的來自其他方言(如“呼舅母日妗子”),有的隨事物消亡而消失(如“總角日拐子頭”)�����。值得注意的是“父日爹,又日別平聲����,又日大”條,父親的稱呼竟有三種之多��,其中“爹”大約是原有的����,“大”可能來自山西,“別平聲”可能來自江淮一帶�,至今山西和江淮一帶仍有這樣稱呼父親的,從中正可以看出當時各地方言對北京話的影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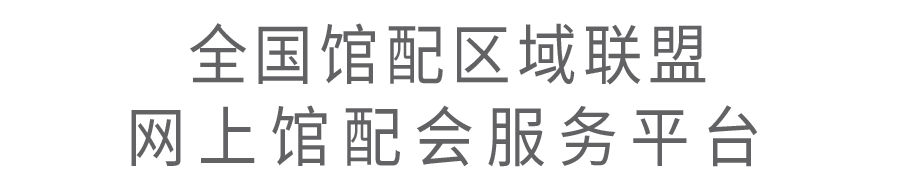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書單推薦
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
新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