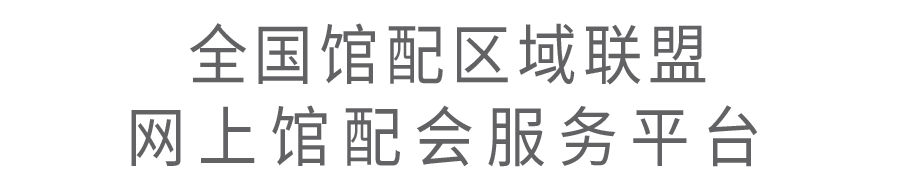1943 Ρξ«ο���Θ§“ΜΈΜ¹μΉ‘±±²êΕΊΓΔΟϊΫ–ΩΥάοΥΙ·ΑΆΩΥΒΡ29 öq«Αύ]Ψ÷¬öÜTΑl(f®Γ)§F(xi®Λn)Ή‘ΦΚ‘Ύάϊ±»¹ÜΚΘΑΕΑΌüoΝΡΌ΅����ΓΘΥϊ ««Α“ΜΡξ»κΈιΒΡΘ§¥ΥïrΖΰ“έ”ΎΆ–≤ΦτîΩΥΗΫΫϋΒΡ”Δ΅χΜ Φ“–≈Χ•≤Ωξ†ΓΘΥϊ≤Δ¦]”–Ω¥ΒΫΧΪΕύëπ(zh®Λn)ΕΖΘΚ≥ΩΨöΦ”“Μ–©κs³’÷°Κσ���Θ§ΥϊΆ®≥Θïΰ»Ξœ¬ΤεΓΔΆφΜίΥΙΧΊ≈Τ�Θ§Μρ’Ώ”^Ω¥èΡ”Δ΅χΕ®ΤΎΏ\¹μΒΡκä”ΑΓΘΥϊΉν¥σΒΡ™ζënΨΆ «άœ σ����ΓΔΧχ‘ιΚΆ…nœâΘΜëπ(zh®Λn)†é‘ΎΚή¥σ≥ΧΕ»…œœώ «÷Μ‘Ύ³eΧéΑl(f®Γ)…ζΒΡ ¬«ι�ΓΘ
ΑΆΩΥΉ‘¨W≥…≤≈Θ§ «“Μ²Äïχ¥τΉ”�����ΓΘΥϊ¥Β΅uΉ‘ΦΚ «ξ†άοΒΡΉνΦ―όq ÷�����Θ§Ά§ïrΏÄ¨ëΝΥ‘SΕύ–≈�����ΓΘΥϊ¨ë–≈ΫoΉ‘ΦΚΒΡΦ“»ΥΚΆ÷°«Αύ]Ψ÷ΒΡΆ§ ¬��Θ§“‘ΦΑ“ΜΈΜΟϊΫ–ςλ≤ΦΒΡΦ“ΉεΙ ”―ΓΘ1943 Ρξ9 ‘¬5 »’��Θ§Ρ« «“Μ²Ä–«ΤΎΧλ��Θ§Υϊ”Ο“Μ²Ä–ΓïrΒΡΩ’ιeïrιgΫo“ΜΈΜΟϊΫ–Ίêήγ·ΡΠ†•ΒΡ≈° Ω¨ëΝΥ“ΜΖβ–≈��ΓΘΊêήγ÷°«Α“≤ «ύ]Ψ÷ΒΡΙώÜT�����Θ§§F(xi®Λn)‘Ύ «ΆβΫΜ≤ΩΒΡ“ΜΟϊΡΠΥΙΟή¥aΤΤΉgÜT�����ΓΘëπ(zh®Λn)†é÷°«Α�����Θ§Υϊ²É‘χΫ¦(j®©ng)±Υ¥ΥΆ®–≈”ë’™’ΰ÷ΈΚΆ¬™(li®Δn)ΟΥÜ•ν}�Θ§“‘ΦΑΗςΉ‘ΒΡ±ßΊ™ΚΆ¨ΠΈ¥¹μΒΡΤΎΆϊΓΘΒΪΥϊ²É÷°ιg“Μ÷±ΕΦ «ΑΊά≠àD ΫΒΡ”―’xΓΣΓΣΊêήγ°îïrΗζ“Μ²ÄΫ–ΡαΩΥΒΡΡ–»ΥΦsïΰ�Θ§Υυ“‘ΩΥάοΥΙ‘ΎèΡάϊ±»¹Ü¨ëΫoΊêήγΒΡΒΎ“ΜΖβ–≈άο’JûιΥϊ²É ««ι²HΓΘΊêήγéΉ²Ä–«ΤΎΚσ¨ëΝΥΜΊ–≈����Θ§»ΜΚσ≤ν≤ΜΕύÉ…²Ä‘¬≤≈ΦΡΒΫ���Θ§ΕχΏ@ΖβΜΊ–≈¨Δ”άΏhΒΊΗΡΉÉΥϊ²ÉΒΡΟϋΏ\ΓΘ
Έ“²É ÷άο≤Δ¦]”–Ώ@Ζβ–≈�����Θ§ΒΪΩ…“‘≈–îύΏ@Ζβ–≈ΩœΕ®üα«ι―σ“γ����ΓΘΒΫΥϊ²ÉΒΎ»ΐ¥ΈΜΞœύΆ®–≈ΒΡïrΚρ����Θ§ο@»ΜÉ…»Υ–Ρ÷–ΕΦ»ΦΤπΝΥüoΖ®ίp“Ή™δ€γΒΡΜπ―φΓΘ≤ΜΒΫ“ΜΡξ�Θ§Ώ@¨Π«ι²H±ψι_ Φ’³Μι’™ΦόΝΥΓΘΒΪ≈c¥ΥΆ§ïr��Θ§Υϊ²É“≤”ωΒΫΝΥ“Μ–©άßκy�����Θ§±»»γ≤ΜΡή’φ’ΐΒΊ“äΟφ�����Θ§Μρ’Ώ€ ¥_”¦ΒΟ¨ΠΖΫΒΡιLœύΓΘΚσ¹μΏÄ≥ω§F(xi®Λn)ΝΥ‘SΕύΤδΥϊΉηΒKΘΚόZ’®�ΓΔ±Μ≤ΕΓΔΦ≤≤Γ��ΓΔΩ…–ΠΒΡ’`ïΰ��ΓΔ≈σ”―ΒΡΖ¥¨Π�����ΓΔ¨Π¨è≤ιΒΡΩ÷ë÷»»����ΓΘ
Υϊ²É÷°ιgΒΡ500 ΕύΖβ–≈ΒΟ“‘±Θ¥φœ¬¹μΘ§±ΨïχΨΪΏx≥ωΤδ÷–Ήν³”»Υ��ΓΔΉνΝν»ΥΗ–≈d»Λ�ΓΔΉνüα«ιΒΡ≤ΩΖ÷ΓΘΏ@ «“Μ¥ΈΝΥ≤ΜΤπΒΡΆ®–≈����Θ§≤Μ÷Ι «“ρûιΥϋ”¦δ¦ΝΥ“ΜΕΈ≤Μ«ϋ≤Μ™œΒΡêέ«ιΙ ¬ΓΘ–≈÷–ΚΝüo±ΘΝτ����Θ§§F(xi®Λn)¥ζΉx’ΏïΰκS÷χΥϊ²É‘Ύüo±MΒΡΩ Άϊ�ΓΔ”ϊΆϊ�ΓΔΩ÷ë÷ΓΔΜΎΚόΦΑΚΝ≤Μ―Ύο½ΒΡ’φ™¥«ιΗ–÷–δζ»Μ€Iœ¬�ΓΘΜρ‘S÷Μ”–Ρ«–©ηF ·–ΡΡcΒΡ»Υ≤≈≤Μïΰ≥–’J‘ΎΏ@üα«ι―σ“γΒΡάΥ≥±÷–’“ΒΫΝΥΉ‘ΦΚΏ^»ΞάΥ¬ΰΒΡ”ΑΉ”�����ΓΘ”––©–≈œΓΥ…ΤΫ≥Θ���Θ§ΒΪ¥σ≤ΩΖ÷ΕΦΚή”ΡΡ§Θ®Έ“ «’fΘ§¨Π”ΎΈ“²É¹μ’fΚή”ΡΡ§��Θ§Εχ¨Π”ΎΥϊ²É¹μ’fο@»ΜΚή÷Ί“ΣΘ©�����Θ§ΕχΥυ”–ΒΡ–≈Ι≤Ά§«…ΟνΕχÉû(y®≠u)―≈ΒΊ”|³”Έ“²É����ΓΘ
Ώ@άοΒΡΫ^¥σΕύîΒ(sh®¥)–≈≥ωΉ‘ΩΥάοΥΙ÷° ÷ΓΘûιΝΥΙù(ji®Π) Γ––Ρ“Ω’ιg�����Θ§Ά§ïr±ήΟβ³e»ΥΗQ“ïΥϊ²ÉΒΡ”HΟήξP(gu®Γn)œΒΘ§ΊêήγΒΡ¥σΕύîΒ(sh®¥)–≈ΕΦ±ΜΩΥάοΥΙüΐΒτΝΥ��ΓΘΒΪΟΩ“Μμ™–≈άοéΉΚθΕΦ «Υΐ����Θ§ΩΥάοΥΙΜΊèΆΥΐΉνΫϋΒΡ”^ϋcΘ§ΨΆΖ¬ΖπΥϊ²É‘ΎœύύèΒΡΖΩιgάοΫΜ’³��ΓΘΈ“²Ééß÷χΩ¥Ζ ‘μ³ΓΑψΒΡΑVΟ‘ΉΖΥϊ²ÉΒΡ–≈����Θ§Ήν¥σΒΡΖ¥≈…ΨΆ «ëπ(zh®Λn)†é±Ψ…μΘ§ΒΎΕΰ¥σΖ¥≈… «Υϊ²É÷ΗΊüΒΡΡ«–© ΙΥϊ²ÉΖ÷ι_ΒΡ»Υ���ΓΘκS÷χΩΥάοΥΙèΡ±±Ζ«Ώw“Τ÷ΝœΘ≈DΚΆ“β¥σάϊΒΡüαϋcΒΊÖ^(q®±)�����Θ§ύ]’ΰΖΰ³’ΒΡ≤ΜΖÄ(w®ßn)Ε®–‘”÷≥…ΝΥ“Μ¥σü©êά���Θ§≤ΜΏ^Θ§Ά®–≈ΨΙ»Μ“Μ÷±¦]”–÷–îύ�Θ§“≤Υψ «²ÄΤφέEΝΥΓΘΈ“²É?y®≠u)ιÉ…»Υ™ζ–Ρ���Θ§Υϊ²É‘Ϋœμ ήΩλ‰Ζ����Θ§Έ“²ÉΨΆ‘ΫΡήνA“äΒΫûΡκyΓΘ
èΡ1943 Ρξ9 ‘¬ΒΡΒΎ“ΜΖβ–≈ΒΫ1946 Ρξ5 ‘¬ΩΥάοΥΙèΆÜT����Θ§ΩΥάοΥΙΚΆΊêήγ÷Μ“äΝΥÉ…¥ΈΟφΘ§Υϊ²ÉΒΡύ]’ΰάΥ¬ΰΟηάLΝΥ“Μ½lîύîύάm(x®¥)άm(x®¥)Ös”÷ °Ζ÷‘ζ¨çΒΡΜΓΨÄ����ΓΘΥϊ²ÉΒΡ‘SΕύ–≈ΕΦ”–ΚΟéΉμ™ιLΘ§άοΟφΏÄ”–‘SΕύ÷ΊèΆΒΡÉ»(n®®i)»ί�����Θ§”»Τδ «Υϊ²É¨Πêέ«ιΒΡΩ Άϊ����Γ���ΘΩΥάοΥΙ≈Φ†•ïΰΑl(f®Γ)±μ¨ΠΙΛïΰ÷ΤΕ»���ΓΔΦ“Ήε’ΰ÷ΈΦΑ άΫγΤ’±ι†νëB(t®Λi)ΒΡιLΤΣ¥σ’™�ΓΘûιΝΥ’Ι Ψ“Μ²Ä÷πùu’Ιι_«““ΐ»Υ»κ³ΌΒΡΙ ¬�Θ§Έ“Ώx™ώ÷Μ±ΘΝτΡ«–©ΉνœύξP(gu®Γn)ΓΔΉν÷Ί“ΣΚΆΉν“ΐ»Υ»κ³ΌΒΡΦöΙù(ji®Π)��ΓΘ“ρ¥Υ���Θ§‘SΕύΩΥάοΥΙ¨ëΒΡ–≈≤Δ¦]”– ’»κ±Ψïχ�����Θ§ΕχΝμ“Μ–©“≤³h€pΒΟ÷Μ ΘéΉΕΈ�����ΓΘ
Ώ@É…²Ä»Υ «’l�ΘΩ‘Ύ”ω“ä±Υ¥Υ÷°«Α����Θ§Υϊ²ÉΉνξP(gu®Γn)–ΡΒΡ÷ς“Σ « ≤Ο¥ΘΩΜτά’ΥΙ·ΩΥάοΥΙΆ–ΗΞ·ΑΆΩΥΘ®ΗΗΡΗΖQΤδûιΓΑΜτ†•Γ±Θ©≥ω…ζ”Ύ1914 Ρξ1 ‘¬12 »’����Θ§“Μ÷±Ώ^÷χΡ«²ÄïrΤΎΒΡΤDΩύ…ζΜνΓΘΥϊΒΡΗΗ”H «“ΜΟϊ¬ö‰I(y®®)ήä»ΥΘ§‘Ύ”ΓΕ»ΚΆΟάΥς≤ΜΏ_ΟΉ¹ÜÖΔΦ”ΝΥΒΎ“Μ¥Έ άΫγ¥σëπ(zh®Λn)�Θ§Κσ¹μ≥…ûι“ΜΟϊύ]ΏfÜTΘ®Η±‰I(y®®) ««εΩ’ΙΪΙ≤κä‘£ΆΛάοΒΡ”≤é≈Θ©Γ�����ΘΩΥάοΥΙΤπ≥θ‘ΎœΡΆΰ“ΡιL¥σ��Θ§Κσ¹μ»ΞΝΥ±±²êΕΊ���Θ§»ΜΚσ «ΨύκxΆ–ΧΊΦ{ΡΖΝυΙΪάοΒΡΒΊΖΫ�����ΓΘ °ΥΡöq“βΆβκxι_Β¬άΉνDΙΪà@¨W–ΘΚσ����Θ§Αύ÷ς»ΈΝτœ¬ΒΡàσΗφάο¨ëΒάΘΚΓΑ“Μ²ÄΖ«≥��ΘΩ…ΩΩΒΡΚΔΉ”�����ΓΔ“Μ²Ä’\¨ç Ί–≈”÷≥ω…ΪΒΡΙΛ»ΥΓ±κxι_ΝΥ�Θ§ΓΑΥϊ‘Ύ–ΘΤΎιg±μ§F(xi®Λn)Éû(y®≠u)°êΘΚ «¨W–ΘΉνÉû(y®≠u)–ψΒΡΚΔΉ”÷°“Μ�����Θ§Υυ”–ΙΠ’nΕΦΆξ≥…ΒΟΚήΚΟΘ§Ζ«≥Θ¬îΟς����ΓΘΓ±
ΗΗ”HûιΥϊ‘Ύύ]Ψ÷¨ΛΝΥ“ΜΖίΙΛΉς��Θ§Ω…“‘œκ“ä�����Θ§Ώ@ «“Μ²ÄΩ…“‘Η…“ΜίÖΉ”ΒΡηFοàΆκ��Γ����ΘΩΥάοΥΙΉν≥θ‘ΎÖRΩνÜΈ≤ΩιTΉω “É»(n®®i)–≈≤νΘ§Υϊ‘Ύύ]Ψ÷≈ύ”•¨W–Θ»ΓΒΟΝΥΝΦΚΟ≥…ΩÉ��Θ§»ΜΚσ‘Ύ²êΕΊ•|Ö^(q®±)’“ΝΥ“ΜΖίΙώÜTΒΡΙΛΉς�����ΓΘΥϊΒΡêέΚΟ «–¬¬³ΚΆΙΛïΰΘ§Ϋ¦(j®©ng)≥Θ‘Ύύ]Ψ÷ΒΡ÷ήΩ·¨ΘôΎ…œ¨ΔÉ…’ΏΚœΕΰûι“Μ�����ΓΘΥϊ≤Μ «≈…¨Π…œΒΡ÷––Ρ»ΥΈο��Θ§ΒΪΫ^¨Π «Εψ‘ΎΫ«¬δάοΒΡ“Μ²ÄΩ…ΩΩΒΡ»Υ���ΓΘ
Υϊο@»Μ≤Μ «Ω®Υ_÷ZΆΏ ΫΒΡάΥ éΙΪΉ”���ΓΘ
ΑΆΩΥ“ΜΦ“‘ΎΕΰëπ(zh®Λn)±§Αl(f®Γ)«Α≤ΜΨΟΑαΒΫΝΥΩœΧΊ≤ΦΝ_ΡΖάϊΒΡΑκΣöΝΔΓΑ³e ϊΓ±Θ§ΩΥάοΥΙ“Μ÷±‘ΎΡ«άο…ζΜνΒΫ1942 Ρξ���ΓΘΥϊΉςûικä²ς¥ρΉ÷ôC≤ΌΉςÜTΥυΫ” ήΒΡ”•Ψö ΙΥϊΡήâρΒΟΒΫ“Μ²Ä±ΘΝτ¬öΈΜ��Θ§Κσ¹μ��Θ§ήäω‘°ΒΡ–η«σ‘Ύ1942 Ρξœ» «¨ΔΥϊéßΒΫΝΥΦsΩΥΩΛΒΡ”•Ψö†I��Θ§»ΜΚσ”÷éßΆυ±±Ζ«�ΓΘ
Ίêήγ·Α§Ν’·ΡΠ†•Θ®Φ“»ΥΚΆ“Μ–©≈σ”―ΖQΥΐάΌΡίΘ©≥ω…ζ”Ύ1913 Ρξ10 ‘¬26 »’����Θ§±»ΥΐΒΡΗγΗγΆΰ†•ΗΞάΉΒ¬–ΓÉ…öqΘ§‘γΡξΉΓ‘ΎΡœ²êΕΊΒΡ≈εΩΥΡΖά≠“ΝΘ®Peckham RyeΘ©����ΓΘΥΐΏÄ”–ΤδΥϊÉ…²Ä–÷ΒήΫψΟΟΘ§ΒΪΕΦ≤Μ–“‘γΊ≤��ΓΘΥΐΒΡΗΗ”HΫ–Άΰ†•ΗΞάΉΒ¬��Θ§ «ύ]Ψ÷άοΒΡΝμ“ΜΈΜΓΑΫK…μ³Ύ“έ’ΏΓ±����ΓΘΊêήγ…œ÷–¨WïrΪ@ΒΟΣ³¨WΫπΘ§“‘Éû(y®≠u)°ê≥…ΩÉΆ®Ώ^ΩΦ‘΅����Θ§»ΜΚσ≥…ûι“ΜΟϊύ]’ΰκäàσÜTΓΘΥΐ’Jûι�����Θ§Ω…Ρή¦]”– ≤Ο¥±»Ώ@²ÄΗϋ÷ΒΒΟ����ΓΔΗϋ≥δùM»Υ«ιΈΕΚΆΕύ‰”–‘ΓΔ÷¬ΝΠ”ΎΙΪΙ≤Ζΰ³’ΒΡΙΛΉς��ΓΘ
1938 ΡξΘ§25 öqΒΡΊêήγκSΦ“»Υ“ΜΤπΑαΒΫ≤Φ»RΩΥœΘΥΦ�ΓΘΡΠ†•“ΜΦ“Ώ^÷χœύ¨ΠΗΜ‘ΘΒΡ…ζΜνΘ§Ε®ΤΎ»ΞΚΘΏÖΕ»ΦΌ����Θ§Εχ«“Ϋ¦(j®©ng)≥ΘΙβνô²êΕΊΈςÖ^(q®±)³Γ‘ΚΓΘΊêήγ”»Τδœ≤ög £≤°Φ{ΚΆΦΣ≤ΖΝ÷ΒΡΉςΤΖ����Θ§Εχ«“êέΚΟà@Υ΅ΚΆ ÷ΙΛΓΘΕΰëπ(zh®Λn)±§Αl(f®Γ)Κσ≤ΜΨΟ���Θ§ΥΐΫ” ήΒΡΡΠΥΙΟή¥a”•Ψö ΙΥΐΪ@ΒΟΝΥ“ΜΖί‘ΎΆβΫΜ≤ΩΤΤΉgΫΊΪ@ΒΡΒ¬΅χüoΨÄκä–≈œΔΒΡΙΛΉς����ΓΘΥΐΫ¦(j®©ng)övΝΥιWκäëπ(zh®Λn)�����Θ§≤Δ≥–™ζΖ≈…ΎΒΡ¬öΊü����Θ§ΏÄ÷Ψ‘ΗΦ”»κΝΥΩ’ήä΄D≈°ίo÷ζξ†Θ§÷±ΒΫ1942 ΡξΡΗ”H»Ξ ά���ΓΘ
Έ“ΒΎ“Μ¥ΈΩ¥ΒΫΩΥάοΥΙΚΆΊêήγΒΡ–≈ «‘Ύ2013 Ρξ4 ‘¬����ΓΘ°îïrΈ“’ΐ‘Ύ³™(chu®Λng)ΉςΈ“ΒΡïχΓΕïχ–≈ΒΡöv ΖΓΖΘ®To the Letter Θ©���Θ§Ώ@±Ψïχ÷ς“Σ «Όùμû’ΐ‘Ύœϊ ßΒΡïχ–≈Υ΅–g(sh®¥)���ΓΘ»ΜΚσΘ§Νν»Υ“βΆβΒΡ «��Θ§Έ“‘Ϋ¹μ‘Ϋ“βΉRΒΫ���Θ§Έ“ΒΡïχάο»±…ΌΒΡ’ΐ «–≈�ΓΘΗϋΨΏσwΒΊ’f���Θ§»±…Ό≥ωΉ‘Τ’Ά®»ΥΕχΖ«Οϊ»Υ÷° ÷ΒΡ–≈�����ΓΘΈ““Μ÷±‘ΎξP(gu®Γn)ΉΔ–ΓΤ’Ν÷Ρα�����ΓΔΚÜ·äWΥΙΆΓ��ΓΔΧΊΒ¬·–ίΥΙ����ΓΔΊàΆθΑΘ†•ΨSΥΙ·Τ’άΉΥΙάϊΘ§≤Δ«““Μ÷±‘ΎΚΆônΑΗ±ΘΙήÜT’³’™��Θ§öv Ζ¨WΦ“²ÉΚήΩλΨΆΒΟΌM³≈ΒΊΆ®Ώ^ΈΡ±ΨΚΆΆΤΧΊΘ®twitterΘ©¹μ”¦δ¦Έ“²ÉΒΡ…ζΜνΝΥ��ΓΘ‘Ϋ¹μ‘Ϋ«ε≥ΰΒΡ“Μϋc «ΘΚΏ@±Ψïχ–η“ΣΒΡ «ΡήâρΒδ–ΆΒΊ±μ§F(xi®Λn)ïχ–≈ΗΡΉÉΤ’Ά®»Υ…ζΜνΒΡ¨çάΐ��ΓΘ
Κσ¹μ�����Θ§Έ“ΆΜ»ΜΫΜΝΥ“Μ¥ΈΚΟΏ\�����ΓΘΈ“‘χœρΥ_»ϊΩΥΥΙ¥σ¨W¥σ±ä”^≤λônΑΗ “ΒΡΙήάμÜTΖΤäWΡ»·Ω®άοΤφΧαΤπΈ“ΒΡïχ�����Θ§ΥΐΖ«≥Θ–≈»ΈΈ“��ΓΘΚσ¹μΘ§ΥΐΧαΒΫΉνΫϋ–¬ΒΫΝΥ“Μ¥σ≈ζξP(gu®Γn)”Ύ“Μ²ÄΫ–ΩΥάοΥΙ·ΑΆΩΥΒΡ»ΥΒΡΌYΝœ���Θ§“Μ¥σΕ―œδΉ”άο―bùMΝΥ–¬¬³àσΒά��ΓΔ’’Τ§���ΓΔΈΡΦΰ�Θ§ΏÄ”–‘SΕύ–≈ΓΣΓΣ“ΜΕ―Αl(f®Γ)ΟΙΒΡΫK…μ’δ≤ΊΓΘΈ“ΝΔΩΧΨΆ»ΞΝΥônΑΗ “���ΓΘ‘ΎΈίάοΩ¥ΝΥ °Ζ÷γäΚσ����Θ§Έ“¥_Ε®Υϊ≈cΊêήγ·ΡΠ†•ΒΡΏ@–©Ά®–≈’ΐ «Έ““Σ’“ΒΡ����ΓΘ≤ΜΒΫ“Μ²Ä–ΓïrΘ§Έ“?gu®©)ΉΚθ“Σ¬δ€IΝΥ���ΓΘ
Ώ@–©ΈΡônΒΡ’δΌF¨Π”ΎΒΎ“Μ²Ä”ωΒΫΥϋ²ÉΒΡöv Ζ¨WΦ“¹μ’f «ο@Εχ“Ή“äΒΡ�����ΓΘΥϊ²ÉΥυ”–ΒΡ–≈éΉΚθΕΦ « ÷¨ë�Θ§”–‘SΕύο@»Μ «¥“ΟΠ÷°ιgΆ¥ΩύΒΊ²}¥ΌΆξ≥…ΓΘΘ®Ά®–≈ «Νμ“ΜΖNΈ“²É?n®®i)γΫώ“―Ϋ?j®©ng)Άξ»ΪÜ ßΒΡ‰Ζ»Λ����Θ§¥σΦ“÷Μ–η“ΣΩ¥“ΜΩ¥ΆβΤΛ…œκs¹yΒΡύ]Τ±ΓΔν}ΈΡΚΆ’fΟςΨΆïΰΟςΑΉ�����Θ§Ώ@–©–≈‘ΎΆΨ÷–≤Δ≤Μμ‰άϊ���ΓΘΘ©ΜΊ¹μ÷°Κσ≤ΜΨΟ�����Θ§Έ“ΨΆΗζΊ™Ίü‘ΎônΑΗ “άοî[Ζ≈ΈΡΦΰΒΡ»ΥΝΡΝΥΝΡ��Θ§’à«σ‘ΎΈ“ΒΡïχάο Ι”ΟΏ@–©–≈��ΓΘΈ“°îïrμ‰ΩΎ’fΝΥΨδ�Θ§¨Δ¹μΏ@–©–≈Ω…Ρή“≤Ω…“‘ΣöΝΔ≥…ïχ�ΓΘΒΟΒΫ‘ ‘SΚσΘ§Έ“èΡΈε °Εύ»fΉ÷ΒΡ–≈Φΰ÷–Ώx»ΓΝΥ¥σΦsÉ…»fΉ÷Θ§¨ΔΤ䥩≤ε‘ΎΈ““―”–ΒΡ’¬Ιù(ji®Π)÷–�����ΓΘ
éΉ²Ä‘¬Κσ��Θ§Έ“ΒΡïχ≥ωΑφ�����Θ§‘SΕύΉx’Ώüα–ΡΒΊ‘ÉÜ•ξP(gu®Γn)”ΎΩΥάοΥΙΚΆΊêήγΒΡΙ ¬�����ΓΘΏÄ”–ΗϋΕύ»Υ’fΥϊ²ÉΧχΏ^ΝΥ÷ς“Σ’¬Ιù(ji®Π)����Θ§ΨΆ «œκ÷ΣΒάΏ@¨Π«ι»ΥΚσ¹μ‘θΟ¥‰”ΝΥ��ΓΘ÷°Κσ≤ΜΨΟ���Θ§ΩΥάοΥΙΚΆΊêήγ≥…ûιΟϊûιΓΕïχ–≈…ζΜνΓΖΘ®Letters Live Θ©ΒΡœΒΝ–±μ―ίΒΡ÷ςΫ«����Θ§‘Ύ±μ―ί÷–Θ§±ΨΡαΒœΩΥΧΊ·ΩΒ≤°ΑΆΤφ��ΓΔ¬Ζ“ΉΥΙ·≤Φάοάϊ�����ΓΔϊê…··Β¬»f�����ΓΔ³Pάρ·Η��ΘΩΥΥΙ�����ΓΔ≈ΝΧΊάοΩΥ·ΩœΡαΒœΚΆ¥σ–l(w®®i)·ΡαΩΥ†•ΥΙΒΡΨΪ≤ ―ίά[Ηϋ «ûιΥϊ²ÉΎAΒΟΝΥΗϋΕύΖέΫz����ΓΘ“ρ¥ΥΘ§Έ“Ω…“‘’φ’\ΒΊ’f��Θ§ëΣ¥σ±ä“Σ«σ��Θ§Ώ@άο «ξP(gu®Γn)”ΎΥϊ²ÉΒΡΙ ¬ΒΡΗϋΆξ’ϊΟη ω�����ΓΘ
èΡΥϊ²ÉΒΡΫΜΝς÷–Θ§Έ“²ÉΩ…“‘¨WΒΫ ≤Ο¥���ΘΩ Ήœ»�Θ§ïχ–≈ΥυΌx”ηΒΡ‰O¥σΒΡ”HΟή–‘ «»ΈΚΈΤδΥϊ•|ΈςΕΦ±»≤ΜΝΥΒΡ���ΓΘΚξ¥σΒΡöv Ζ¦]”–ïrιg»ΞξP(gu®Γn)ΉΔΖ±Εύ±χ…αάοΒΡêά»ΥΦöΙù(ji®Π)���Θ§Μρ «ëπ(zh®Λn)ïr≤Μ–“ΒΡΌèΈο––ûιΘ§Ηϋ≤Μ”Ο’fΒΆΒ»ëπ(zh®Λn)ΕΖ»ΥÜTΒΡΡ§Ρ§ΖνΪI�����ΓΘΒΪ≥ΐΝΥ¥σΟΑκU÷°Άβ��Θ§ΉνΉ¨Έ“²ÉΨΨ–ΡΒΡ «Ώ@–©≈ΦΑl(f®Γ) ¬ΦΰΘΚκä”Α÷–ά≠Ϋπ ΫΒΡ ßΆϊ����ΘΜ«ΑΆ§Αι“ρΦΒΕ ΕχΚ§…≥…δ”Α��ΘΜ“ΐνI(l®Ϊng)ïr…–ΒΡüτ–ΨΫq―ùΉ”����ΘΜùuùu…ν»κλ`ΜξΒΡΤDΩύ���ΘΜΖ®΅χΒΡάΉ”ξ¨ß÷¬ΒΡύ]’ΰ―”’`Ω…ΡήïΰΉ¨“Μ²Ä»ΥΖ«≥Θ™ζ–ΡΓΘ
Τδ¥Έ��Θ§Υϊ²É‘Ύ–≈÷–±μ§F(xi®Λn)≥ω¹μΒΡüα«ι±»±Ψ»ΥΗϋ³Ό�ΓΘΩΥάοΥΙ“Μ¥Έ¥ΈΧαΒΫΚσΜΎ‘ΎÉ…»Υ÷–ιg“äΟφïr���Θ§Ή‘ΦΚΫY(ji®Π)ΫY(ji®Π)ΑΆΑΆ����ΓΔ‘~≤ΜΏ_“β���ΓΘΥϊ²É…ζ³”ΒΡ±μΏ_Ω…Ρή‘Ύ“ΜΕ®≥ΧΕ»…œΨèΫβΝΥΡ«ΖN¦Q»ΜΒΡΤύ¦ωΘ®ΓΑΈ“²É÷ßΝΥ²ÄéΛ≈ώ���ΓΘΈ“²ÉΑ―éΛ≈ώ≤πΝΥΓ����ΘΓ±ëπ(zh®Λn)†éΫY(ji®Π) χïrΘ§±≥Ί™÷χΡ«–©ΡξΥυ”–ΜΡèUΒΡöq‘¬�Θ§ΩΥάοΥΙΏ@‰”¨ëΒάΘ©����ΓΘ
Έ“¥_–≈‘ΎΈ¥¹μéΉΡξάο�Θ§Έ“²Éïΰσ@Τφ”÷ι_–ΡΒΊΉx÷χΏ@–©–≈ΓΘΏ@άοΦ»”–“Μ–©Τφ¬³“ί ¬��Θ§“≤”–“Μ–©»’≥�����Θ§ç ¬����ΓΘΩΥάοΥΙΚΆΊêήγûι÷°ΪI…μΒΡύ]’ΰΖΰ³’ΉνΫKΜΊàσΝΥΥϊ²ÉΓΣΓΣ“‘ΦΑΈ“²É�ΓΘ‘ΎΥϊ²Éïχ–≈Ά®«ιΒΡ‘SΕύΡξΚσΘ§Ώ@¨Π«ι²H“Μ÷±Μν÷χ÷v ωΥϊ²ÉΒΡΙ ¬���ΓΘΒΪΥϊ²ÉèΡ¹μ¦]”–Ώ@‰”÷vΏ^����ΓΘ
Ώ@άοΟφΉνΈϋ“ΐΈ“ΒΡ“ΜϋcΨΆ «¦]”–”Δ–έ�ΓΘΈ“²ÉΒΡïχ–≈ «¥ύ»θΒΡ�����ΓΔΩ÷ë÷ΒΡΘ§”–ïr…θ÷Ν «≥δùMΏzΚΕΒΡ�����ΓΘΥϊ²ÉΫ¦(j®©ng)≥ΘΊü²δΉ‘ΦΚΒΡΥΦœκΚΆ––ûι���ΓΘΒΪΚήκyœκœσΏÄ”–±»Ώ@Ηϋ÷±Ϋ”�����ΓΔΗϋΧλ’φ�����ΓΔΗϋ¬ΰüoΏÖκH�����ΓΔΗϋΆξ»ΪΧΙ’\ΒΡΫΜΝς�����ΓΘ°îëπ(zh®Λn)†éΏÄ‘Ύά^άm(x®¥)ïr���Θ§Ώ@¨Π«ι²H÷Τ‘λΝΥΥϊ²ÉΉ‘ΦΚΒΡρ}³”�ΓΘ°îè½ΜπùMΧλοwïr�����Θ§Υϊ²ÉΉ‘ΦΚΒΡρ}³”≥…ΝΥΜνœ¬»ΞΒΡΗϋèä¥σΒΡάμ”…�ΓΘΈ“œκ’fΒΡ «Θ§κm»Μ‘Ύ«πΦΣ†•ΒΡ¥σ―ί÷v÷–≤Δ¦]”––ϊ≤Φ��Θ§ΒΪΈ“²É «ûιΩΥάοΥΙΚΆΊêήγΏ@‰”ΒΡ»ΥΕχëπ(zh®Λn)�ΓΘ≈cΤδ’f «ûιΝΥξ•ΙβΤ’’’ΒΡ”Δ΅χΡΝàωΘ§≤Μ»γ’f «ûιΝΥΉ¨œύêέΒΡ»Υ²É‘ΎΡΝàω…œàFΨέΒΡΉ‘”…�����ΓΘ
Ψé’Ώ
ΈςΟ…??Φ”ΖΤ†•Β¬Θ®Simon GarfieldΘ©
”Δ΅χΈΡ¨W¥σΣ³ΟΪΡΖΣ³Ϊ@ΒΟ’Ώ���Θ§Ι≤³™(chu®Λng)Ής °Εύ≤Ω÷χΟϊΒΡΖ«–Γ’fνêΉςΤΖ����Θ§¥ζ±μΉς”–ΓΕïχ–≈ΒΡöv ΖΓΖΘ®÷––≈≥ωΑφ…γ≥ωΑφΘ©ΓΖΓΕΈ“²ÉΒΡκ[ΟΊ…ζΜνΓΖΓΕëπ(zh®Λn)†é÷–ΒΡΈ“²ÉΓΖΒ»��Θ§§F(xi®Λn)Ψ”²êź»º���ΓΘ
Ής’Ώ
ΩΥάοΥΙ??ΑΆΩΥΘ®Chris BarkerΘ©
°ΥΡöqι_ Φ±ψ‘Ύύ]Ψ÷ΙΛΉς�����Θ§Ήνι_ Φ «“ΜΟϊΥΆ–≈ΒΡΙΛΉς»ΥÜT���Θ§÷°Κσ≥…ûιΝΥύ]Ψ÷ΒΡ“ΜΟϊΈΡÜTΘ§ΥϊΏÄ «“ΜΟϊΜνήSΒΡΙΛïΰïΰÜT��ΓΘ‘ΎΒΎΕΰ¥Έ άΫγ¥σëπ(zh®Λn)ΤΎιg�����Θ§Υϊ‘ΎΖ«÷ό±±≤Ω™ζ»ΈΝΥ“ΜΟϊ–≈Χ•ÜT�����ΓΘ
Ίêήγ??ΡΠ†•Θ®Bessie MooreΘ©
‘ΎΏM»κΆβΫΜ≤ΩΙΛΉς÷°«Α «ΩΥάοΥΙ??ΑΆΩΥ‘Ύύ]Ψ÷ΒΡΆ§ ¬�Θ§Υΐ‘ΎΡΣ†•ΥΙ¥aΖΫΟφΫ” ήΏ^¨ΘιTΒΡ”•ΨöΘ§‘ΎΕΰëπ(zh®Λn)ΤΎιgΥΐΒΡΙΛΉςΨΆ «Ζ≠ΉgΫΊΪ@ΒΫΒΡΒ¬΅χκä≈_ΒΡ–≈œΔ�����ΓΘ
Ήg’Ώ
èà‘¥
±±Ψ©¥σ¨WΖ≠Ήg¥T Ω��Θ§‘χΖ≠ΉgΓΕ”ά≤Μ―‘½âΓΖΓΕ“ΜΦ”“ΜΓΖΓΕΗφ‘Vά«²ÉΈ“ΜΊΦ“ΝΥΓΖΒ»Εύ≤ΩΉςΤΖΓΘ
«Α ―‘ 01
01ΓΓ≈f»’≈σ”―‘θΡήœύΆϋ 001
02ΓΓΈ“²É“ΜΤπ��Θ§ùM–Ρögœ≤ 027
03ΓΓΡψ «Έ“œκΜΊΦ“Ήν÷Ί“ΣΒΡ‘≠“ρ 053
04ΓΓ “‘Έ“÷°–’ΙΎΡψ÷°Οϊ 079
05ΓΓ÷±ΒΫΈ“²Éœύêέ���Θ§Έ“²É≤≈ΥψΜν÷χ 101
06ΓΓΏ@άοΒΡΚ§–Ώ≤ίΕΦι_ΝΥ�����Θ§ΒΪΡψ‘Ύ”Δ΅χ 123
07ΓΓΈ“ïΰΑ≤»Ϊöw¹μ����Θ§ΜΊΒΫΡψ…μΏÖ 143
08ΓΓ“ΜΕ®“ΣΧαΫY(ji®Π)Μι 175
09ΓΓΈ“²É“―Ϋ¦(j®©ng) «ΖρΤόΝΥ�Θ§
≤Μïΰ“ρûι†é≥≥Εχ ß»Ξ±Υ¥Υ 209
10ΓΓ–Γ’δΡίΧΊΏÄ «–ΓΩΥάοΥΙΆ–ΗΞΘΩ 217
11ΓΓΡψΨΆ‘ΎΏ@²Ä άΫγ…œ�����Θ§÷Μ «œύΗτ«ß»fάο 239
12ΓΓΈ“ΫK”ΎΧΛ…œöwΆΨ��Θ§»ΞΡψΒΡë―άο 261
ΨéΚσ”¦ 286
ΫY(ji®Π)’Z 297
Ψé’ΏΒΡ‘£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