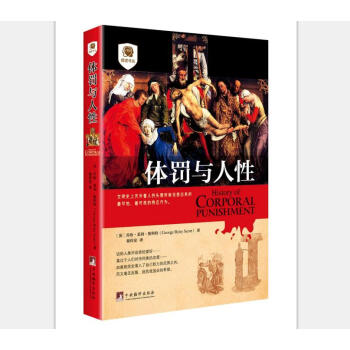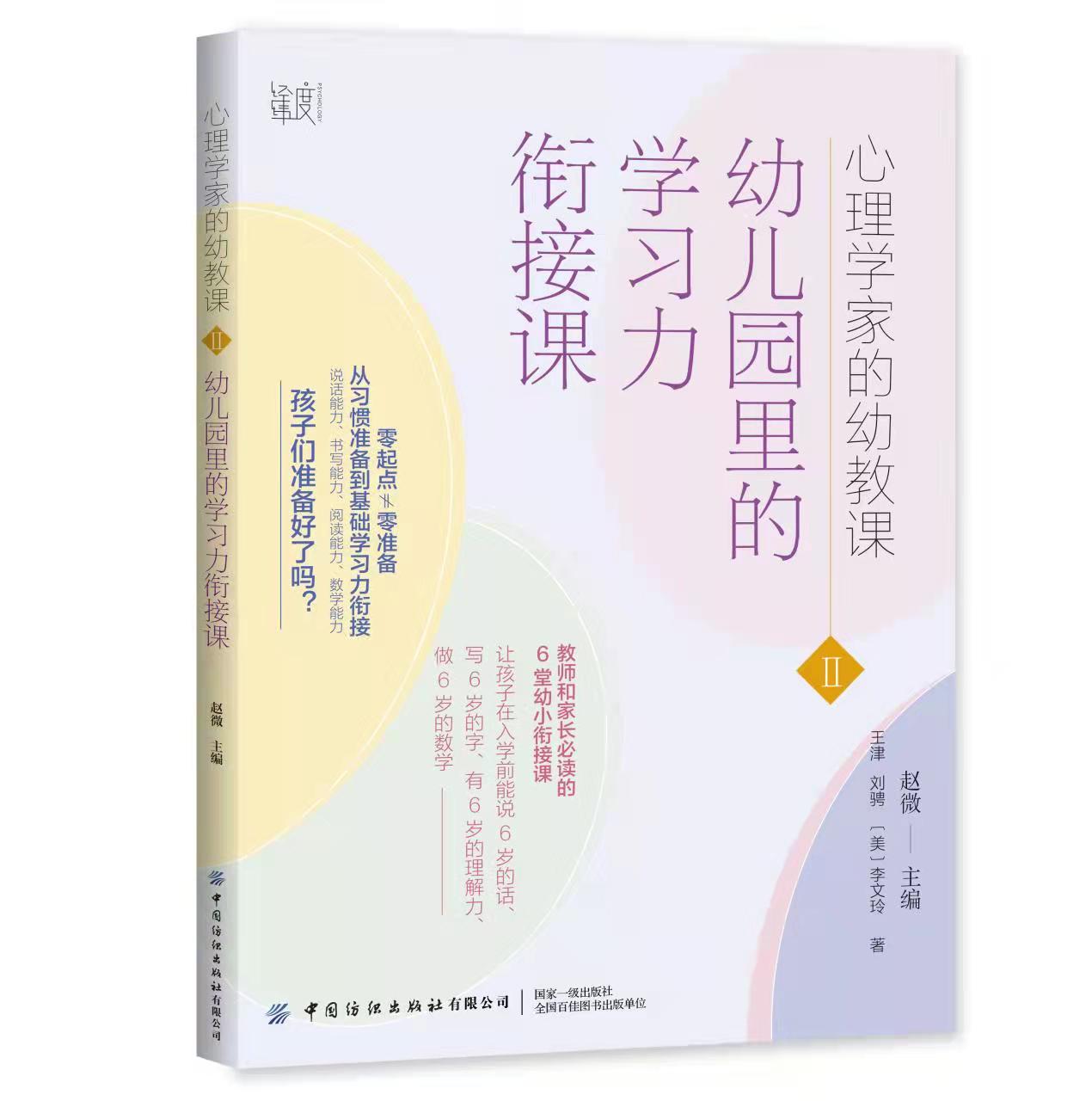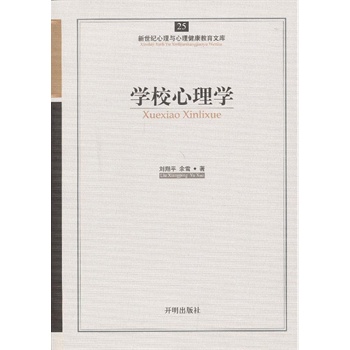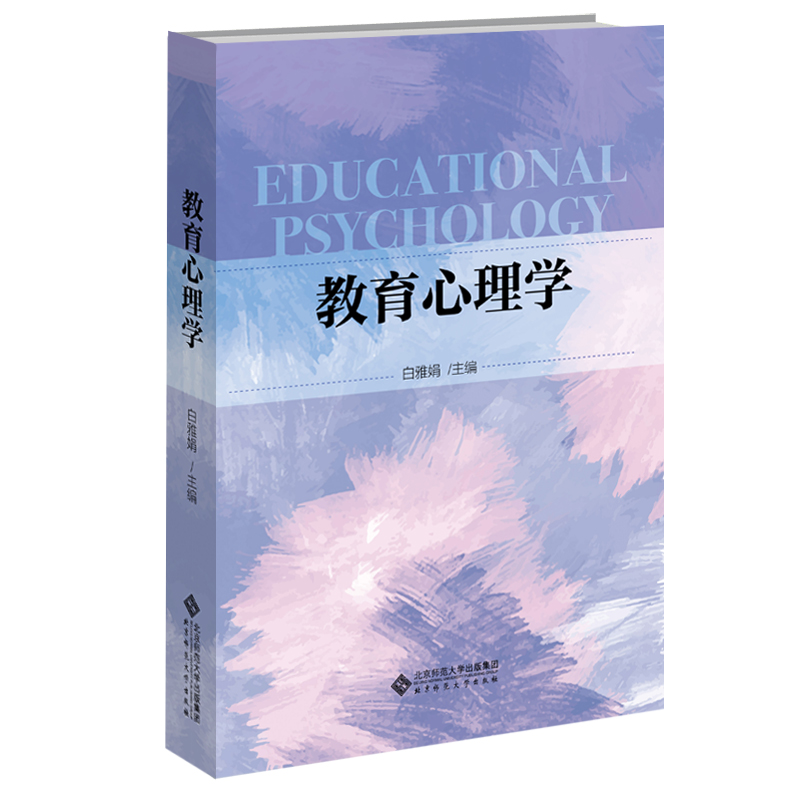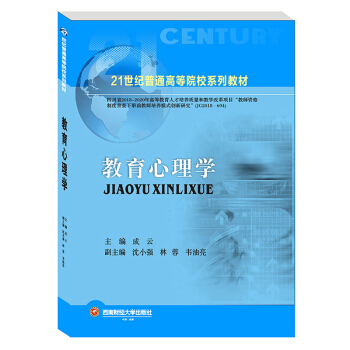өЪТ»Іҝ·ЦұЮуЧөДРДАнҢW(xuЁҰ) / 1
өЪ1ХВИЛоҗЕcЙъҫгҒнөДҡҲИМ / 3
өЪ2ХВУдҗӮЕcМЫНҙ№ІЙъ / 9
өЪ3ХВ»щұҫ„УҷCЈәУРТвЧRөДәНҹoТвЧRөД / 12
өЪ4ХВҢҰНҙҝаөДЦОҜҹәНЛҺОп№ҰР§ / 17
өЪ¶юІҝ·ЦРМБPөДұЮуЧ / 23
өЪ5ХВұЮуЧРЎНөәНјЛЕ®өИИЛ / 25
өЪ6ХВұЮуЧЕ«л`әНЖНИЛ / 50
өЪ7ХВЬҠк ЦРөДұЮуЧ / 61
өЪ8ХВјТНҘәНҢW(xuЁҰ)РЈҢҰәўЧУөДұЮуЧ / 71
өЪИэІҝ·ЦЧЪҪМЦРұЮуЧ / 83
өЪ9ХВРЮөАФәАпөДұЮуЧ / 85
өЪ10ХВЧФОТұЮуЧ / 92
өЪ11ХВұЮуЧХЯҪМЕЙ / 103
өЪ12ХВЧЪҪМ·ЁНҘЕcұЮуЧ / 111
өЪ13ХВёжҪвЙсёёЕcұЮуЧ / 120
өЪЛДІҝ·ЦЦ§іЦЕc·ҙҢҰуwБPөДАнУЙ / 125
өЪ14ХВ‘НБPөДРДАнҢW(xuЁҰ) / 127
өЪ15ХВұЮуЧҢҰіЙИЛөДЙнРДУ°н‘ / 133
өЪ16ХВұЮуЧҢҰЙЩДкөДЙнРДУ°н‘ / 140
өЪ17ХВЕcұЮуЧУРкP(guЁЎn)өДЧпҗә / 148
өЪ18ХВуwБPөДІЎ‘B(tЁӨi)·ҪГж / 162
өЪ19ХВҪY(jiЁҰ)Х“ / 183
өЪ3ХВ
ҡҲИМөД„УҷCИЛоҗН¬°ыәН„УОп®”ЦРөДМЫНҙЎўРЯИиәНҝалy�Ј¬һйКІГҙ•юФЪК©јУДЗР©ҡҲИМРРһйөДИЛЙнЙПҶҫЖрУдҗӮ����ЈҝДҝ¶ГДі·NРОКҪөДұ©РРһйКІГҙ•юҪoЕФУ^ХЯҺ§ҒнУдҗӮ���ЈҝЯ@Р©¶јКЗЙоҠW¶шлyҪвөДҶ–о}�ЎЈЛьӮғёъИзҙЛЦ®¶аөДЙз•юТтЛШәНРДАнТтЛШ»мФЪБЛТ»Жр�����Ј¬ТФЦБУЪәЬлyҪoУиЦұҪШБЛ®”?shЁҙ)ДҪвҙрЎ?/p>
ОТӮғТСҪӣ(jЁ©ng)ҝҙөҪ��Ј¬ФЪТ°РUөДФӯКј·NЧеЦР��Ј¬ҡҲИМөШЕ°ҙэ‘р(zhЁӨn)·э�����ЎўЕ«л`�Ўў”іИЛј°ЖдЛыёчЙ«ИЛөИөДУ^ДоЈ¬КЗУЙУЪЛьЧчһйТ»·NНю‘ШБҰБҝөДғrЦө¶ш®a(chЁЈn)ЙъөД��ЎЈОТӮғҝҙөҪ���Ј¬ФЪОДГчЙз•юАп�Ј¬Я@Т»»щұҫУ^ДоИзәОөГТФ°l(fЁЎ)Х№Ј¬ЦұЦБИЛӮғФO(shЁЁ)УӢіцБЛМҺБPТҺ(guЁ©)„t����Ј¬ТФҢҰё¶ёч·NІ»Н¬өД·ёЧпәНРРһйІ»¶ЛЎЈФЪЛщУРЧчһйТ»·N‘НБPРОКҪ¶шК©јУөДХЫДҘ»тҡҲИМРРһйөДұіәу���Ј¬ұнГжөДТвҲDКЗТ»·NХэБxЎӘЎӘЦБЙЩФЪОДГчЙз•юАпКЗЯ@ҳУ�Ў���Ј»щ¶ҪҪМ•rҙъЛщК©РРөДЛщУРҝЙЕВөД���ЎўБоИЛХру@өДҡҲИМРРһйЈ¬¶јКЗТФөАөВәНИЛөАөДЙсКҘГыБx¶шУиТФҢҚК©өД��ЎЈһйБЛИЛГсөДАыТж�Ј¬Т»ЦұКЗЖИәҰХЯөД‘р(zhЁӨn)¶·ҝЪМ–Ј¬ТІКЗЛыӮғРРһйөДХэ®”АнУЙ�ЎЈө«КЗЈ¬Я@Т»ҪвбҢКЗХжөДГҙ����ЈҝҢҰҙЛОТЙоұн‘СТЙ���ЎЈ
УРТ»·NУ^До����Ј¬КАКАҙъҙъөГөҪИЛӮғөДЦ§іЦЈ¬ІўК№Ц®УАҙжІ»Ра���Ј¬Я@ҫНКЗЈә·Ё№Щ����ЎўЖИәҰХЯ�Ўў„ЈЧУКЦЎӘЎӘәҶСФЦ®Ј¬ҫНКЗГҝТ»ӮҖТФИОәО·ҪКҪёъҢҚК©ИОәОРОКҪөД‘НБPВ“(liЁўn)ПөФЪТ»ЖрөДИЛЎӘЎӘ¶јКЗФЪТ»·NҮАёс¶шҝМ°еөДХэБxёРөДтҢ(qЁұ)К№ПВРР„У�ЎЈЯ@јғҢЩЧУМ“һхУРЎЈУРТ»ьcө№КЗХжөДЈә”іИЛәН‘СУР”іТвөДҡvК·ҢW(xuЁҰ)јТ¶јғAПтУЪНЁЯ^НкИ«І»Н¬өДНёзRҒнҝҙҙэЯ@Р©ЛщЦ^өДХэБxЦ®Еe�Ј»ө«ФЪ®”•rЈ¬ЛыӮғҙуҷа(quЁўn)ФЪОХөДН¬°ы¶јХJһй���Ј¬ХэБxКЗјӨ°l(fЁЎ)ГҝТ»РР„УөД„УҷC��ЎЈ
¬F(xiЁӨn)ФЪ���Ј¬ЖІй_·ЁВЙәНХэБxІўІ»КЗТ»ҙaКВЯ@ӮҖКВҢҚІ»Х„���Ј¬иbУЪФшҪӣ(jЁ©ng)УРЯ^өДГҝТ»Іҝ·ЁВЙ¶јКЗУЙДЗР©ФЪДіР©·ҪГжҢҰҢҚК©·ЁВЙёРЕdИӨөДӮҖИЛЛщФO(shЁЁ)УӢіцҒнІўХэКҪЕъңКөДЈ¬ОТӣ]·ЁН¬ТвЯ@ҳУТ»ӮҖУ^ДоЈәГҝӮҖ·Ё№ЩәН„ЈЧУКЦ¶јКЗТтһйӣQРДТӘЧҢХэБxөГөҪЙмҸҲ��Ј¬¶шІ»КЗТтһйИОәОЖдЛыАнУЙ���Ј¬ІЕЧ·ЗуЛыӮғёчЧФөДВҡҳI(yЁЁ)���ЎЈјҙК№УЙУЪДі·NҷCҫүЈ¬ЛыӮғЧоіхҝЙДЬКЗҺ§ЦшЦTИзҙЛоҗөДДҝөДЦшКЦ№ӨЧчөД�Ј¬ө«ҺЧӮҖФВөДҪӣ(jЁ©ng)ҡvҫНЧгТФЧҢЛыӮғПаРЕЈәЯ@ӮҖПл·ЁКЗТ»ӮҖЙсФ’Ј¬Т»ӮҖеeУX����Ј¬¶шЗТЈ¬ЛыӮғ•юФЪ…’җәәНҪ^НыЦР·Е—үЧФјәөД№ӨЧч���ЎЈДгНкИ«ҝЙТФВ•·Q��Ј¬ДБҺҹҝӮКЗҺ§ЦшЯ@ҳУТ»·NХжХ\өДРЕДоЯx“сЧФјәөДВҡҳI(yЁЁ)�ЎўІўҲФіЦІ»РёөШҸДКВЦ®ЈәЛыФЪ’юЯxДЗР©ҸДҙулyЦРөГҫИөДИЛ���Ј¬ІўК№м`»кҺ§ЦшқҚғфөДБјРДәН»ЪёДөДТвФёЯMИлМмҮш�ЎЈ
Из№ыДгПЈНыёьјУҪУҪьХжПаЈ¬ДЗГҙДгЧоәГКЗ’Ғ—үЯ@ҳУТ»ӮҖУ^ДоЈәөДҙ_ҙжФЪЦTИзјғҙвАыЛыЦчБxЦ®оҗөД–|Оч�����ЎЈИОәОТ»ӮҖИЛЛщЧцөДЙЖКВ���Ј¬ҺЧәхҝӮКЗЕјИ»өДЈ¬¶шЗТФЪДі·NТвБxЙПКЗұ»ЖИөД����Ј¬КЗЛыФЪһйБЛДіӮҖДҝөД¶шЧцөДДіјюКВЗйІ»ҝЙұЬГвөШ°йлS°l(fЁЎ)ЙъөДКВЈ¬¶шЯ@ӮҖДҝөД��Ј¬ёъЯ@јюҙуҙөҙуАЮөД��Ўўө«ҢҚлHЙПКЗ°йлS°l(fЁЎ)ЙъөДЙЖКВНкИ«І»ҙоҪз����ЎЈшBғәіФөфұЗМйПxЈ¬ҪoЮr(nЁ®ng)ГсТФУРТжөДҺНЦъ����Ј¬ө«ҫНҪY(jiЁҰ)№ы¶шСФЈ¬ЛьӮғІўӣ]УРЧФХJһйФЪТФИfДЬЙПөЫөДГыБxЧцЦшЙЖКВ��ЎЈЮr(nЁ®ng)ГсһйЛьӮғҙуіӘЩқёиЈ¬ө«ФЪ·NПВ·NЧУөДДЗТ»ҝМ��Ј¬Лы…sГИЙъБЛ»ДЦҮҝЙРҰөД»ГПл��Ј¬ТӘЕ¬БҰҮҳЕЬЛыФшҪӣ(jЁ©ng)өДГЛУС�����ЎЈТӘКЗЛыҝҙТҠТ»Ц»№ВБгБгөДВйИёФЪФҮҲDЯMИлЯ@үKЙсКҘөДоI(lЁ«ng)өШ�����Ј¬ЛыҫН•юФ{ЦдЛьИҘЛА�Ј¬ІўСёЛЩөШЙмКЦИҘДГЛыөДҳҢЎЈШҲДГәДЧУ��Ј¬УРИЛХJһйДЗКЗИКҙИөДЙПөЫһйБЛЯ@Т»МШКвөДДҝөД¶ш„“(chuЁӨng)ФмБЛЯ@·N„УОп��Ј»ө«Из№ыУРҷC•юөДФ’����Ј¬Ль•юН¬ҳУёЯёЯЕdЕdөШІ¶ҡўҪрҪzИёәНРЎлuЈ¬ЛьӮғөДЦчИЛНщНщ•юТФІ»Н¬өД‘B(tЁӨi)¶ИҒнҝҙҙэШҲөДЯ@Р©ПыЗІ����ЎЈоҗЛЖөД���Ј¬Ң§(dЁЈo)ЦВДРИЛәНЕ®ИЛЎӘЎӘҫНҪ^ҙу¶а”ө(shЁҙ)¶шСФЎӘЎӘИҘЧцЯ@јюКВЗй»тНЖ„УДЗјюКВЗйЎўИҘёъР°җә‘р(zhЁӨn)¶·��ЎўИҘ°l(fЁЎ)ЖрёДёпөД»щұҫ„УҷC���Ј¬ёъЛыӮғ№«й_Ры·QөДДЗР©ДҝҳЛӣ]УРИОәОкP(guЁЎn)Пө����ЎЈҢҚлHЙП���Ј¬ИОәОТСҪӣ(jЁ©ng)ҢҚ¬F(xiЁӨn)өДіЙ№ҰЈ¬¶јёҪҢЩУЪЯ@ӮҖ»щұҫөД��Ўўө«л[ІШЦшөД»тль–VІ»ЗеөДДҝҳЛ����ЎЈ
®”И»Ј¬»щұҫөД„УҷCЦчТӘКЗ’кЙъ»о���ЎЈФЪОДГчЙз•ю�Ј¬ҢӨЗуәНРиТӘ№ӨЧчөДИЛ�����Ј¬¶аУЪМṩҪoЛыӮғөД№ӨЧчҚҸО»Ј¬ТтҙЛ�����Ј¬Я@ӮҖ»щұҫ„УҷCКЗТ»ӮҖЧоҸҠҙуөД„УҷC���ЎЈҙу¶а”ө(shЁҙ)ИЛәЬЙЩУРҷC•юЯx“сТФәО·N·ҪКҪ’көГЛыӮғөДЙъҙжұШРиЖ·�����Ј»оҗЛЖөД�����Ј¬ЛыӮғТ»ө©Яx“сБЛ»тХЯұ»ЖИҪУКЬБЛТ»·ЭВҡҳI(yЁЁ)»тРР®”����Ј¬ЛыӮғҫНІ»өГІ»ЎӘЎӘІ»№ЬФёТвІ»ФёТвЎӘЎӘФЪЯ@Т»ВҡҳI(yЁЁ)»тРР®”ёЙПВИҘ���Ј¬ЦұөҪЛыӮғ?nЁЁi)лНБһй°І���Ј¬»тХЯФЪЛҘРаЦ®ДкНЛРЭ���ЎЈХэКЗУЙУЪЯ@ӮҖФӯТтЈ¬ІЕУРДЗГҙ¶аИЛФчәЮЛыӮғ?yЁӯu)йБЛЙъУӢ¶шөГөҪөД№ӨЧч��ЎЈКВҢҚЙП�����Ј¬Я@ӮҖХf·Ё¶а°лЯmУГУЪИ«КАҪз°Щ·ЦЦ®ҫЕК®өД№ӨИЛ���ЎЈЯҖУРТ»Р©ИЛ����Ј¬ЛыӮғТІФчәЮЧФјәөД№ӨЧч��Ј¬ө«һйБЛДіӮҖІ»Н¬УЪјғҙв·eАЫШ”ё»өДФӯТт���Ј¬ЛыӮғҺ§ЦшұнГжЙПөДҹбЗйәНХжХ\ҸДКВЛыӮғөД№ӨЧчЎЈЯ@Р©ЙЩ”ө(shЁҙ)ИЛҝЙТФФЪДіӮҖЖдЛыөДРРҳI(yЁЁ)’көГЧФјәөДЙъ»о��Ј¬»тХЯЛыӮғҝЙДЬУРЧгүт¶аөДеX��Ј¬К№ЛыӮғНкИ«УГІ»Цш№ӨЧч����Ј¬ө«һйБЛДіР©ЛыӮғІ»ПлПтКАИЛХ№КҫөДФӯТт����Ј¬АэИзҝКНыҷа(quЁўn)БҰ»тГыВ•���Ј¬»тХЯҝКНыҢӨ»ЁҶ–БшөДҷC•ю�����Ј¬ЛыӮғПЈНыА^Аm(xЁҙ)ҸДКВЛыӮғЛщЯx“сөДМШ¶ЁВҡҳI(yЁЁ)»тРР®”���ЎЈ
әЬлyПлПуТ»ӮҖ„ЈЧУКЦ•юПІҡgЧФјәөД№ӨЧчЈ¬»тХЯТ»ӮҖұO(jiЁЎn)ӘzҝҙКШ��Ј¬Т»ӮҖҫҜІм���Ј¬Т»ӮҖНА·тЎӘЎӘ®”И»�����Ј¬іэ·ЗЛыКЗӮҖК©Е°ҝс�ЎЈН¬ҳУәЬлyПлПуЈ¬Т»ӮҖКХ¶җ№ЩДЬүтҸДЛыөДЯ@·ЭАХЛчН¬°ыөД№ӨЧчЦР«@өГҝмҳ·ЎӘЎӘЖдЦРәЬ¶аН¬°ыӣ]УРДЬБҰАUј{ЛщТӘЗуөД¶җҝоЎӘЎӘХэИзЛыЗеіюөШЦӘөАөДДЗҳУ���Ј¬Я@ҳУКХҒнөДеXЦ»І»Я^КЗһйБЛЧҢДЗР©УЮҙАөД№ЩҶTҝЙТФЛБТв“]»ф��ЎЈёьлyПлПуөДКЗ�Ј¬Т»О»ЦО°І·ЁНҘөДВЙҺҹ•юТФЧФјәөДКВҳI(yЁЁ)һйҳ·����Ј¬ФЪЯ@ӮҖРР®”АпЈ¬ЛыіЈіЈұ»ЖИҫнИлҙуТҺ(guЁ©)ДЈөДХfЦe�ЎўӮОЙЖәНЖЫт_Ц®ЦРЎЈ
әЬИЭТЧ°СХэБxЕcҲуҸН(fЁҙ)ёг»мПэ���ЎЈФвКЬБЛИЛЙнӮыәҰ»тХЯУЙУЪЛыИЛөДРРһй¶шіРКЬБЛ“pК§өДДРИЛәНЕ®ИЛ���Ј¬ҝӮКЗХжХ\өШҝКНыҢҰҙЛШ“УРШҹ(zЁҰ)ИОөДӮҖИЛКЬөҪ‘НБPЈ»¶ш‘НБPөДіМ¶ИЕcЛыЛщ·ёПВөДЧпРРПа·Q���Ј¬ТӘГҙНЁЯ^ЧФјәөДҲуҸН(fЁҙ)Ц®КЦЈ¬ТӘГҙҪиЦъ·ЁВЙЦ®КЦ��ЎЈјИИ»ИзҙЛ����Ј¬ДЗГҙјӨ°l(fЁЎ)ИЛӮғҝКНыҪoУи·ёЧпХЯТФЯm®”‘НБPөД„УҷC����Ј¬ІўІ»КЗКІГҙІ»Һ§ӮҖИЛёРЗйЙ«ІКөДҢҰХэБxөДҹбҗЫ����Ј»ХэПа·ҙЈ¬ЛьјғҙвКЗҢҰӮҖИЛҲуҸН(fЁҙ)өДҝКНы��ЎЈҫНҙу¶а”ө(shЁҙ)Зйӣr¶шСФ�����Ј¬®”Я@№PӮҖИЛЩ~ұ»ҪY(jiЁҰ)ЗеөД•rәт��Ј¬ҢҰ‘НБP����ЎўӮыәҰЎўК©јУНҙҝаөДҸҠБТҝКНыТІұгПыК§өГТ»ёЙ¶юғф�����ЎЈ
ТтҙЛ���Ј¬ОТӮғҝЙТФ°СјғҙвҹбҗЫХэБxЧчһйТ»·N‘НБP„УҷCөДУ^ДоТ»№P№ҙдN����Ј¬ТтһйЛьҢҚлHЙПІўІ»ҙжФЪЈ»¶шЗТ���Ј¬ОТӮғҝЙТФХJһй����Ј¬ҫНҪ^ҙу¶а”ө(shЁҙ)УРҷC•юТФХэБxөДГыБxҢҚК©ҡҲИМРРһйөДИЛ¶шСФ��Ј¬ҙЩК№ЛыӮғРР„УөДЦчТӘ„УҷCТІКЗ’кЙъ»о���ЎЈЛыӮғұ»№НӮтҒнҲМ(zhЁӘ)·Ё�����Ј¬¶шЗТЛыӮғТА“ю(jЁҙ)Йз•юЛщХJҝЙ»тЕъңКөД·ЁВЙТҺ(guЁ©)„tҒнҲМ(zhЁӘ)·Ё�����Ј¬јҙК№Я@ёъЛыөДӮҖИЛҗЫәГПаөЦУ|���ЎЈЛыӮғҲМ(zhЁӘ)·ЁөД•rәтГчҙ_өШЦӘөАЈәИз№ыОҙДЬВДРРЯ@Т»ВҡШҹ(zЁҰ)Ңў•юҢ§(dЁЈo)ЦВЮoНЛЈ¬¶шЗТ����Ј¬ЧчһйҢҰЧФјәБјРДөДТ»ьc°ІОҝЈ¬ЛыӮғҝӮКЗМбіцЯ@ҳУТ»ӮҖуaЕKөДХ“ьcЈәјҙК№ЛыӮғІ»ЧцҙЛКВөДФ’��Ј¬„eИЛТІ•юЧц�ЎЈ
ХэИзОТЛщХfЯ^өДДЗҳУЈ¬Я@Р©ИЛҳӢ(gЁ°u)іЙБЛҙу¶а”ө(shЁҙ)���ЎЈө«ЯҖКЗУРЙЩ”ө(shЁҙ)ИЛТФ‘НБPН¬°ыһйҳ·����Ј¬»тХЯҳ·УЪДҝ¶ГЛыӮғКЬөҪ‘НБP����Ј»ХэИзУРР©ИЛТФЕ°ҙэ„УОпһйҳ·»тҳ·УЪДҝ¶Г„УОпФвЧпТ»ҳУЎЈОДГчЙз•юТІҙжФЪК©Е°ҝсәНРФЧғ‘B(tЁӨi)��ЎЈәЬ¶аЯ@ҳУөДДРДРЕ®Е®ФЪұO(jiЁЎn)Әz���ЎўёР»ҜФә»тНАФЧҲцАпөГөҪБЛЧФјәөД№ӨЧч���ЎЈ
ЕcЯ@Р©Чғ‘B(tЁӨi)ХЯУРьcкP(guЁЎn)В“(liЁўn)өДКЗ�����Ј¬УРР©ИЛПІҡgДҝ¶Г»тПлПуДі·NПуХчРОКҪөДҡҲИМРРһйЎӘЎӘЯ@ҳУТ»·NРОКҪФЪ¬F(xiЁӨn)ҙъОДГчЦРёщЙоөЩ№М�����Ј¬ХэИзДбІЙФЪПВГжЯ@¶ОБоИЛлyНьөДОДЧЦЦРЛщЦёіцөДДЗҳУЈәОТӮғ·QЦ®һйЎ°ёЯөИОД»ҜЎұөДҺЧәхГҝТ»ҳУ?xЁҙn)|Оч�����Ј¬¶јКЗ»щУЪҢҰҡҲИМРРһйөДҫ«Йс»ҜәНҸҠ»ҜЎӘЎӘЯ@ҫНКЗОТөДХ“ьc���Ј»Ў°Т°«FЎұёщұҫӣ]УРұ»ҡўЛАЈ¬ЛьТ»Цұ»оЦш����Ј¬ЛьТ»Цұ·ұКўЕdНъЈ¬ЛьЦ»КЗёДЧғБЛНвРО���ЎЈДЗҳӢ(gЁ°u)іЙБЛұҜ„ЎЦРөДНҙҝаЦ®ҳ·өД–|Оч����Ј¬ҫНКЗҡҲИМ�Ј»ФЪЛщЦ^Ў°ҢҰұҜ„ЎөДН¬ЗйЎұЦР�Ј¬ФЪГҝТ»јюізёЯКВОп����ЎўЦұЦБЧоёЯјү��ЎўЧоОўГоөДРО¶шЙПҢW(xuЁҰ)ҝмёРөДөЧЧщЙП���Ј¬ДЗБоИЛУдҗӮөШ°l(fЁЎ)“]ЧчУГөД–|Оч���Ј¬Ц»І»Я^КЗҸДҡҲИМөД»мәПОп®”ЦРЈ¬«@өГБЛЛьөДМрГА·Т·ј��ЎЈ ёҘАпөВАпПЈ·ДбІЙЈәЎ¶і¬ФҪЙЖҗәЎ·ЈЁBeyond Good and EvilЈ©�Ј¬Ӯҗ¶ШЈ¬1909����ЎЈЯҖУРТ»Р©ӮҖИЛЎӘЎӘФЩТ»ҙОҢЩУЪЙЩ”ө(shЁҙ)ЕЙЈ¬ө«ФЪГҝТ»ӮҖҮшјТ¶јҝЙТФХТөҪ�Ј¬Из№ыҸДҝӮуwЙПҝјБҝөДФ’”ө(shЁҙ)БҝҙуөГу@ИЛЎӘЎӘНЁЯ^ұ»ИЛұЮҙт¶шҪӣ(jЁ©ng)ҡvРФөДҝмёРәНҙМјӨЎЈЖІй_ДЗР©Ц»УРФЪҪoУи»тҪУКЬ‘НБP•rІЕДЬҪӣ(jЁ©ng)ҡvРФјӨЗйөДК©Е°ҝсәНКЬЕ°ҝсІ»Х„��Ј¬ұЮҙтЕcРФЦ®йgөДВ“(liЁўn)ПөКЗИзҙЛГЬЗР�Ј¬ТФЦБУЪБнНвЯҖУРәЬ¶аИЛЎӘЎӘУИЖдКЗАПДкИЛЎӘЎӘЛыӮғНЁЯ^УРЦъУЪРФӣ_„УәНРФДЬБҰөДұЮҙтҒнҢӨХТҙМјӨ�����ЎЈ
ЧоәуәНЧоЦШТӘөДКЗ�����Ј¬ҙжФЪЯ@ҳУТ»ӮҖТтЛШ���Ј¬ЛьёъПаҢҰҡҲИМөДИОәОҝјБҝУРЦшМШКвөДУ°н‘Ј¬јҙ���Ј¬ҢҰЧФјәЛщКмПӨөДНҙҝаЎӘЎӘҹoХ“КЗИЛөДНҙҝа����Ј¬ЯҖКЗ„УОпөДНҙҝаЎӘЎӘАдД®ҹoЗй���Ј¬ВйДҫІ»ИК����ЎЈХэКЗТтһйЯ@ӮҖТтЛШ���Ј¬·Ё№Щ��ЎўРРРМХЯ��ЎўДҝ“фХЯТФј°ЖдЛыГҝТ»ӮҖёъХЫДҘ�����ЎўҡҲИМәНІ»ИЛөАөДРРһйУРИОәОВ“(liЁўn)ПөөДИЛ�Ј¬¶јИзҙЛҪӣ(jЁ©ng)іЈөШІ»ғHЧғөГФҪҒнФҪҹoЗй���Ј¬¶шЗТЯҖЧғөГФҪҒнФҪҮА…–ЎӘЎӘЦ»ТӘФЪЧФјәөДҷа(quЁўn)БҰ·¶ҮъЦ®ғИ(nЁЁi)�ЎЈкP(guЁЎn)УЪЯ@Т»ьc����Ј¬Ій –Л№·JӘұј{ЖӨ –ЙЩҢўөДФuХ“ЦөөГФЪЯ@АпТэУГТ»ПВЈәУРИЛЧўТвөҪЈ¬®”ИЛӮғШ“Шҹ(zЁҰ)К©јУИОәО‘НБPөД•rәтЈЁІ»№ЬҫНЖдРФЩ|(zhЁ¬)¶шСФЯ@·N‘НБP¶аГҙБоИЛ…’җәЈ©�����Ј¬ЛыӮғНЁіЈЧғөГҝКНыФцјУЛьөДҮА…–ЈәЛыӮғөДРДДcТтһйҝӮКЗДҝ¶ГК©јУЯ@ҳУөД‘НБP¶шЧғөГФҪҒнФҪУІ�����Ј¬ЛыӮғеeХ`өШПаРЕЈ¬ЛыӮғН¬°ыөДЙнуwН¬ҳУЧғөГФҪҒнФҪУІ���ЎЈТӘјmХэЯ@·NЛЖәхКЗОТӮғМмРФЦРЕcЙъҫгҒнөДҡҲИМғAПт����Ј¬ҫНұШнҡЧҢАнРФҪйИл�Ј¬·с„tөДФ’Ј¬ОТӮғөДРДДcҫН•юНЁЯ^СЫҫҰЧғөГПсд“иFТ»ҳУҲФУІ�����ЎЈ Ій –Л№·JӘұј{ЖӨ –ЈәЎ¶Х“ЬҠ·ЁЕcұЮРМЎ·ЈЁRemarks on Military Law and the Punishment of FloggingЈ©���Ј¬Ӯҗ¶Ш��Ј¬1837�Ј¬өЪ146н“���ЎЈөЪ4ХВ
ҢҰНҙҝаөДЦОҜҹәНЛҺОп№ҰР§бt(yЁ©)ҢW(xuЁҰ)����ЎўҪӯәюАЙЦРәНГФРЕТ»Цұұ»лy·ЦлyҪвөШ»мәПФЪТ»Жр��ЎЈјҙК№өҪҪсМмЈ¬ұM№ЬУРҝЖҢW(xuЁҰ)өДҝаРДҪӣ(jЁ©ng) I��Ј¬ө«ЛьӮғТАИ»ФЪәЬҙуіМ¶ИЙПұ»»мһйТ»Х„�����ЎЈТ»ӮҖ•rҙъөДбt(yЁ©)ҢW(xuЁҰ)°l(fЁЎ)¬F(xiЁӨn)��Ј¬ЪAөГБЛИЛӮғөДёЯВ•ЩқГАәНҹбБТҡgәф�����Ј¬…sіЙБЛПВТ»ӮҖ•rҙъөДГФРЕ��Ј¬ФЩЯ^Т»ҙъҫНіЙБЛЙсФ’���ЎЈФЪТ°РUИЛЦРйgЈ¬ОЧбt(yЁ©)ұ»ҡwоҗһйІҝВдөДбt(yЁ©)Йъ�ЎЈЛыКЗ«@өГФSҝЙөДҲМ(zhЁӘ)ҳI(yЁЁ)ХЯЎӘЎӘёъОДГчҮшјТөДбt(yЁ©)ҺҹІ»Н¬өДКЗЈ¬ЛыөДФSҝЙҲМ(zhЁӘ)ХХКЗЙсоC°l(fЁЎ)өД����ЎЈө«Я@Іўӣ]УРёДЧғЯ@ҳУТ»ӮҖКВҢҚЈәҢҚлHЙПЈ¬ФӯКјөДОЧбt(yЁ©)ҫНКЗҪӯәюАЙЦР�Ј»ХэИзОДГчЙз•юЦРәЬ¶аоI(lЁ«ng)УРҲМ(zhЁӘ)ХХөДбt(yЁ©)ЙъТІКЗҪӯәюАЙЦРТ»ҳУЎЈ
®”Ў°Ҫӯәюбt(yЁ©)Рg(shЁҙ)ЎұЯ@ӮҖХf·Ёұ»‘Ә(yЁ©ng)УГУЪбt(yЁ©)ҢW(xuЁҰ)өД•rәтЈ¬ЦчТӘЦёөДКЗ°СДіТ»ӮҖ»щұҫФӯ„t»тҜҹ·ЁҝдҙуһйёъҢҚлHКВҢҚәБІ»ПаёЙөД–|Оч�ЎЈФЪЭpОўМЫНҙөДЗйӣrПВДЬЖрөҪҫҸҪвЧчУГЎў»тХЯДЬЦОәГДіР©ЭpОўјІІЎөДЛҺОп»тЛҺІЭ�����Ј¬ұ»ҝдҙуһй°ьЦО°ЩІЎөДИfм`ГоЛҺ����ЎЈЯ@ҫНКЗҪӯәюбt(yЁ©)Рg(shЁҙ)өДұҫЩ|(zhЁ¬)ЎЈЯmУГУЪДі·Nҹб°YөД»щұҫФӯ„t����Ј¬ұ»ҝдҙуһйЯmУГУЪЖдЛыГҝТ»·Nҹб°YЎЈЯ@ЯҖКЗҢЩУЪҪӯәюбt(yЁ©)Рg(shЁҙ)�����ЎЈ
ОТӮғТСҪӣ(jЁ©ng)ҝҙөҪ����Ј¬ФЪДіР©ЗйӣrПВЈ¬МЫНҙКЗТ»·NҙМјӨәН»оБҰЦ®Фҙ��ЎЈОТӮғҝҙөҪБЛ��Ј¬ФЪМЫНҙәН‘ҚЕӯөДУ°н‘ПВЈ¬ИЛӮғЛщДЬүтЧцөҪөДКВЗй���Ј¬ЯhЯhі¬Я^ЛыӮғФЪЖҪіЈЗйӣrПВЛщДЬЧцөҪөДКВЗй�ЎЈОТӮғЦӘөА��Ј¬Т»ӮҖИЛјҙК№КЗұ»ӮыәҰөГҝмТӘЛАБЛ��Ј¬¶шҫНФЪДЗТ»ҝМ���Ј¬ЛыДЬүтЧціцЧоәуөДЕ¬БҰ�����Ј¬Я@КЗЛыФЪИОәОЖҪіЈЗйӣrПВ¶јНкИ«ЧцІ»өҪөД���ЎЈОТӮғЯҖЦӘөА����Ј¬ФЪ„УОпөДЙнЙПіЈіЈ°l(fЁЎ)ЙъТ»ДЈТ»ҳУөДКВЗйЎЈ
ФзФЪЎ¶КҘҪӣ(jЁ©ng)Ў·ЛщУӣКцөДДкҙъ�Ј¬№ЕИЛҫНҹoТвЦР°l(fЁЎ)¬F(xiЁӨn)БЛЯ@Р©»щұҫКВҢҚЎӘЎӘЛыӮғЧўТвөҪЈ¬ФЪДіР©ЗйРОПВ�Ј¬МЫНҙід®”БЛТ»·NҙМјӨОп�����ЎЈЦұҒнЦұИҘ��Ј¬·ыәПҸД№ЕЦБҪсКАҪзёчөШЎ°ЦЗИЛЎұөДБ•(xЁӘ)‘T��Ј¬ЛыӮғҪУЦшФЪЯ@Т»»щөA(chЁі)ЙПҪЁБўБЛҝдҸҲ�����ЎўЙсФ’әНҪӯәюбt(yЁ©)Рg(shЁҙ)өДХыӮҖҙулs Z�����ЎЈҪУПВҒн��Ј¬ЛыӮғЦчҸҲІў·оРРПВГжЯ@ӮҖјЩХfЈәК©јУМЫНҙ•юФЪЛщУРЗйӣrПВҙМјӨЛщУРДРИЛәНЕ®ИЛөД»оБҰ�����ЎЈТтһйЦШ“фұіІҝУР•rәтДЬЖрөҪЦОҜҹҗһҡвөДЧчУГ���Ј»ЛыӮғұгХJһйЈәЦШ“фОёІҝДЬЦОҜҹұгГШЈ¬ұЮҙтТ»ӮҖЕ®ИЛөДНОІҝДЬҺНЦъЛэ·ЦГд��Ј¬ёоЖЖјзІҝКЗЦОҜҹСЫјІөДЦчТӘ·Ҫ·ЁЎЈ
іэБЛЯ@Р©Т»°гөДјЩХfЦ®Нв����Ј¬ИЛӮғЯҖХJһйЈ¬№ч°фұҫЙнұ»ЩxУиБЛЙсЖж¶шГШГЬөДБҰБҝ��ЎЈЛьКЗТ»·NБҰБҝөДПуХч��Ј»ёьУРЙхХЯ��Ј¬ЛьЯҖКЗкҺЗoөДПуХч��Ј¬ҢҚлHЙПКЗТ»ӮҖұ»ЖХұйҫҙО·әНЧрЦШөДҢҰПу�ЎЈ
ФЪФӯКј·NЧеЦРЈ¬әЬ¶ајІІЎұ»ХJһйКЗУЙУЪР°м`Ң§(dЁЈo)ЦВөД����ЎЈФЪЎ¶КҘҪӣ(jЁ©ng)Ў·ЦРЈ¬Я@ӮҖУ^ьcұ»ФЩИэЦШЙк�����ЎЈұЮҙтКЗтҢ(qЁұ)іэЯ@Р©җәД§»тР°м`өДТ»·NіЈТҠ·Ҫ·Ё����Ј»ДЬүт?qЁұ)§ЦВМЫНҙөДЖдЛыОе»Ё°ЛйTөД‘НБPТІКЗИзҙЛЎЈТтҙЛ�Ј¬Ў¶сRҝЙёЈТфЎ·ЦРЯ@ҳУХfЈәТ®·dТ»ПВҙ¬Ј¬ҫНУРТ»ӮҖұ»ОЫ№нёҪЦшөДИЛ����Ј¬ҸДүһүLАпіцҒнУӯЦшЛыЎЈДЗИЛіЈЧЎФЪүһүLАп�Ј¬ӣ]УРИЛДЬАҰЧЎЛыЈ¬ҫНКЗУГиFжңТІІ»ДЬ���ЎЈТтһйИЛҢТҙОУГД_зӮәНиFжңАҰжiЛы�����Ј¬иFжңҫ№ұ»Лы’к”аБЛ����Ј¬Д_зӮТІұ»ЛыЕӘЛйБЛ�ЎЈҝӮӣ]УРИЛДЬЦЖ·ьЛы����ЎЈЛы•ғТ№іЈФЪүһүLАпәНЙҪЦРә°ҪРЈ¬УЦУГКҜо^ҝіЧФјә�ЎЈЈЁЎ¶РВјs·сRҝЙёЈТфЎ·өЪ5ХВөЪ2Ў«5№қ(jiЁҰ)Ј©Н¬ҳУ����Ј¬°ўЛ№ҝЛАЧұУ°ўөВ�����ЎўҝЁБфЛ№·ҠWАЧАыҒҶЕ¬Л№�ЎўМбҲDЛ№ЎўАЧОчЛ№әННЯАХЛ№ҺмЛ№¶јҪЁЧh°СұЮуЧЧчһйЦОҜҹҫ«ЙсеeҒyөД·Ҫ·Ё���Ј»З§°ЩДкҒн�����Ј¬Я@·NРЕДоФЪәЬ¶аөШ·ҪөГөҪБЛҸҠУРБҰөДЦ§іЦ����ЎЈБ_сRИЛТФһй�����Ј¬ұЮуЧ•юҢ§(dЁЈo)ЦВЕ®ИЛ‘СФР��Ј»¶шЗТ��Ј¬ФЪДЗДко^���Ј¬ЙъғәУэЕ®ҫНКЗЕ®ИЛөДұ§Ш“�����Ј¬ТІКЗЛэөДЛЮГь���Ј¬ТтҙЛЈ¬ЛэҺЧәхКЗқMРДҡgПІөШҡgУӯИЛјТЧбЛэ�����ЎЈ“ю(jЁҙ)ҫSјӘ –әНЛыөДЧўбҢХЯИыҫSһхЛ№Хf���Ј¬ФЪДБЙс№қ(jiЁҰ)ЙП����Ј¬ДіР©МфЯxіцҒнөДДРИЛ�Ј¬Г“өГіа—l—lТ»ҪzІ»’мЈ¬КЦАпДГЦшЖӨұЮ����Ј¬СШЦшҙуҪЦРЎПпТ»В·КЦОиЧгөё�Ј¬УГЖӨұЮійҙтЛыӮғЛщУцөҪөДГҝТ»ӮҖЕ®ИЛ��ЎЈЯ@КЗТ»ӮҖҡvҙъКўРРөДГФРЕөДАэЧУ��ЎЈБнТ»ӮҖАэЧУКЗ№ЕҙъЛ®КЦӮғ®”ЦРКўРРөДТ»ӮҖУ^ДоЈәұЮҙтіЛҝН•ю·АЦ№пL(fЁҘng)ұ©�����ЎЈФЪЕеМШБ_ДбһхЛ№өДЎ¶Л_өЩАыҝЧЎ·ЈЁSatyriconЈ©ЦР��Ј¬ЦvөҪБЛ¶чҝЖ –ЖӨһхЛ№әНјӘоDКЗИзәОұ»ИЛҺ§ЦшЯ@Т»Гчҙ_ДҝөД¶шұЮҙтөД�����ЎЈ•шЦРЯ@ҳУХfЈәЛ®КЦӮғЧціцӣQ¶Ё���Ј¬ТӘҪoОТӮғГҝИЛ40ұЮ�Ј¬һйөДКЗ°І“бЯ@ЛТҙ¬өДКШЧoЙс�ЎЈҪY(jiЁҰ)№ыЈ¬Т»ҝМТІӣ]УРөў”R���Ј¬‘ҚЕӯөДЛ®КЦӮғұгй_КјУГЛыӮғКЦАпөДА|АKійҙтОТӮғ�Ј¬ҳOБҰЧҢЧоұ°ЩvөДСӘБчіцҒнЈ¬ТФҙЛ°І“бКШЧoЙс��ЎЈЦБУЪОТ��Ј¬ОТ°ӨБЛИэұЮ�����Ј¬ОТТФЛ№°НЯ_ИЛөДҢ’әкҙуБҝИМКЬБЛЯ@Р©���ЎЈИыДщҝЁМбіцБЛТ»ӮҖҝӮуwРФөДкҗКцЈ¬У°н‘БЛәЬ¶аФзЖЪЧчјТҢҰјІІЎј°ЖдЦОҜҹөДҝҙ·Ё�����ЎЈЛыХfЈәЎ°®”К§ИҘЦӘУXөДЙнуwұ»МҺАнөГДЬүтёРЦӘМЫНҙөД•rәт��Ј¬бt(yЁ©)ҢW(xuЁҰ)ТІҫНй_КјТҠР§БЛ���Ў����ЈЎұЛыЯҖҪЁЧh°СұЮҙтЧчһйЦОҜҹ°l(fЁЎ)ҹэөДТ»·NМШКвКЦ¶О�ЎЈЖдЛыИЛЧсСӯБЛЛыөДВ·ҫҖЈ¬әЬҝмЈ¬ДЗР©»јЙПБЛПсЖЖӮыпL(fЁҘng)�ЎўМм»ЁЎўпL(fЁҘng)қсәНДcІЎЯ@ҳУТ»Р©ҸV·ә”UЙўөДјІІЎөДИЛ�Ј¬°l(fЁЎ)¬F(xiЁӨn)ЧФјәҝӮКЗұ»ИЛНҙҙтЈ¬һйөДКЗЧҢЛыӮғ®a(chЁЈn)ЙъМЫНҙёР�ЎЈ“ю(jЁҙ)Д«ҺмОчҒҶАыЛ№ХfЈ¬І»№вКЗЙwӮҗҪЁЧh°СұЮҙтЧчһйТ»·NҙЩК№йLИвөДКЦ¶О����Ј¬әЬ¶абt(yЁ©)Йъ¶јй_іцБЛН¬ҳУөДЛҺ·ҪЎЈЗ§°ЩДкҒн����Ј¬Е«л`ЙМИЛТ»ЦұБ•(xЁӘ)‘TУЪұЮҙтЛыӮғөД·эМ”Ј¬ЖдГчҙ_өДДҝөД���Ј¬ҫНКЗҙЩК№ЛыӮғйLИв��Ј¬әГЧҢЛыӮғФЪКРҲцЙПДЬЩIӮҖәГғrеX�ЎЈ
“ю(jЁҙ)»щКІХf әЈТтАпПЈ·»щКІЈәЎ¶Е®ИЛөДРФЙъ»оЎ·ЈЁThe Sexllal Lite of WomanЈ©��Ј¬Ӯҗ¶Ш���Ј¬1910���ЎЈ���Ј¬№ЕПЈЕDУРТ»ӮҖБ•(xЁӘ)ЛЧЈ¬ӢDЕ®Из№ыФЪҪY(jiЁҰ)»йо^ҺЧДкӣ]ЙъәўЧУ�����Ј¬ЛэҫНТӘИҘСЕөдөДЦмЦZЙсҸR��ЎЈФЪДЗАп����Ј¬Т»О»ЕЛЙсөДјАЛҫҢў•юЦОҜҹЛэөДІ»Уэ°Y�ЎЈһйБЛЯ@ӮҖДҝөДЈ¬Лэ·оГьГ“өГТ»ҪzІ»’м�����Ј¬ё№ІҝіҜПВЖҪЕP�Ј¬јАЛҫУГЙҪСтЖӨЦЖіЙөДұЮЧУійҙтЛэЎЈҺЧәхУГІ»Цш‘СТЙ���Ј¬Я@Р©ЕЛЙсөДјАЛҫЕјИ»°l(fЁЎ)¬F(xiЁӨn)��Ј¬ұЮҙтНОІҝ•юҙМјӨРФУыЈЁ…ўТҠөЪ17ХВЈ©����ЎЈ
ұЮуЧҪӣ(jЁ©ng)іЈФЪ№«№ІФЎКТАпЯMРРЎЈАЧёсј{өВХf����Ј¬ІЁөДДбҒҶУРТ»ӮҖЯ@ҳУөДБ•(xЁӘ)ЛЧЈәЕ®әўТӘійҙтЛэӮғіаЙнВгуwөДДРРФРЦөЬЈ¬һйөДКЗЧҢЛыӮғй_ё[���Ј¬ХTК№ғИ(nЁЁi)ЕKЕЕР№���ЎЈ®”И»Ј¬әЬУРҝЙДЬ��Ј¬Я@МЧіМРтФЪДіР©ЗйӣrПВҝЙДЬ•юТҠР§����Ј¬ө«ҳOУРҝЙДЬөДКЗЈ¬ХжХэөДДҝөДКЗРФ·ҪГжөД��ЎЈұШнҡУӣЧЎөДКЗ���Ј¬ДЗДко^ЛщУРөД№«№ІФЎКТҢҚлHЙП¶јКЗјЛФә��ЎЈ
№ЕҙъөДбt(yЁ©)ЙъәНХЬҢW(xuЁҰ)јТХJһй��Ј¬ұЮҙтһйүӢИлҗЫәУМṩБЛТ»н—УР°СОХөДЦОҜҹЮk·Ё�ЎЈҫНЯ@Т»ьc¶шСФЈ¬ЛыӮғЛЖәхёьУРөААн�����ЎЈАЧОчЛ№�����ЎўҝЁБфЛ№·ҠWАЧАыҒҶЕ¬Л№�ЎўНЯАХЛ№ҺмЛ№����ЎўНЯАХЛ№ҺмЛ№әН№ПғИ(nЁЁi)АпһхЛ№өИИЛИ«¶јұ§іЦЯ@Т»РЕДоЎЈФЪСbІЎ��Ўў‘Р¶иәНЖЫт_өДЗйРОПВ�����Ј¬ЛьөДР§БҰТІКЗҝЙРЕөД���ЎЈ
ГФРЕёщЙоөЩ№М��Ј¬ҹoХ“КЗёъЧЪҪМУРкP(guЁЎn)өД�Ј¬ЯҖКЗёъбt(yЁ©)ҢW(xuЁҰ)УРкP(guЁЎn)өДЎЈУЙУЪЯ@ӮҖФӯТт��Ј¬ОТӮғУГІ»Цшҙуу@РЎ№ЦЈәәЬ¶аЯ@ҳУөДУ^До���Ј¬ұM№ЬәЬҙЦІЪ��Ј¬…sҡvҪӣ(jЁ©ng)З§°ЩДкӘqҙж�����ЎЈТ»ӮҖГыҪР°ННРБЦөДИЛФЪ1669ДкҢ‘өАЈәХэИзОТФЪЎ¶ҡvК·лsЧлЎ·ЈЁCento of HistoriesЈ©Т»•шЦРЛщЧCГчөДДЗҳУ����Ј¬ФЪТтМKІјАЧИЛ®”ЦР���Ј¬ИЛӮғНЁЯ^УГБҰ”Dүә¶ЗЧУ����Ј¬»тХЯУГДҫЗт»тиFЗт“фҙтЈ¬ҸД¶ш°СЛАИҘөДМҘғәҸДДёУHөДуwғИ(nЁЁi)ИЎіц���ЎЈОТЯҖЧўТвөҪ�Ј¬ИЛӮғНЁЯ^ұЮҙтҒнЦОҜҹДЗР©ДтҙІөДәўЧУЈЁҙуИЛТІТ»ҳУЈ©�ЎЈ јsәІ·әаАы·Г·І©ГЧһхЛ№ЈәЎ¶Х“ұЮуЧФЪбt(yЁ©)ҢW(xuЁҰ)әНРФУыЦРөДК№УГЎ·ЈЁA Treatise on the Use of Flogging in Medicine and VeneryЈ©ЎЈФЪЎ¶ёР»ҜФәөДғИ(nЁЁi) –Ў·ЈЁNell in BridewellЈ©Т»•шЦР�����Ј¬УӣКцБЛФЪөВҮшөДТ»ЧщұO(jiЁЎn)ӘzАп���Ј¬ЯtЦБ1848ДкЯҖТтһйЯzДт¶шұЮҙтТ»ӮҖәўЧУ����ЎЈЧчһйЦОҜҹДРИЛк–рфәНЕ®ИЛІ»УэөДТ»·NЮk·Ё����Ј¬ұЮҙтФЪ»щ¶ҪҪМуwЦЖҪЁБўЦ®әуөДҺЧ°ЩДкАпТ»ЦұПнУРКўГы����ЎЈФЪЯ@Р©·ҪПтЙПЈ¬ХэИзОТӮғЙФәуҢўТӘҝҙөҪөДДЗҳУ�Ј¬Г·І©ГЧһхЛ№КЗЖдР§БҰөДЦТҢҚРЕНҪЈ»°ўұИ·хUАпҠWТІКЗИзҙЛ�ЎЈЯtЦБ1839Дк���Ј¬ГЬБЦёщЯҖФ”ұMҹoЯzөШҢ‘өҪБЛұЮҙтЦОҜҹјІІЎөД№ҰР§Ј¬Ц§іЦ№ЕИЛөДАнХ“���ЎЈЛыХfЈәұЮҙтЖИК№Сӯӯh(huЁўn)ҸДОТӮғЙнуwПөҪy(tЁҜng)өДЦРРДЧЯПтНвҮъ�ЎЈОТӮғТСҪӣ(jЁ©ng)ЦӘөА�����Ј¬ФЪҜ‘јІ°l(fЁЎ)ЧчЦРЛьҝЙТФтҢ(qЁұ)Йў°l(fЁЎ)АдЖЪ�ЎЈЙwӮҗФшЧўТвөҪЈ¬сRЖҘЙМИЛБ•(xЁӘ)‘TУЪНЁЯ^Яm¶ИөДұЮ“фК№ЛыӮғөДсRЖҘұм·КуwүС���Ј»ІўТтҙЛҪЁЧhУГЯ@·NЮk·ЁҪoКЭЧУФц·К��ЎЈ°І–|ДбһхЛ№·ДВЛ_УГЯ@·NЮk·ЁЦОәГБЛҠW№ЕЛ№¶јөДЧш№ЗЙсҪӣ(jЁ©ng)Нҙ�����ЎЈЕБ¶аНЯЕ¬Л№ҪЁЧh�Ј¬®”ХоІЎұ¬°l(fЁЎ)МҺУЪҫҸВэөД°l(fЁЎ)Х№лA¶ОөД•rәтК№УГұЮуЧ»тКnВйҙМјӨ·Ё�ЎЈНРсRЛ№·ҝІЕБғИ(nЁЁi)АӯУӣдӣБЛТ»О»јқКҝөДІЎАэЈ¬Из№ыІ»КВПИҪУКЬТ»оDұЮҙтөДФ’Ј¬ЛыөДДcөАҫНӣ]·ЁЕЕР№���ЎЈИЛӮғіЈіЈЧўТвөҪ��Ј¬ЖӨДw°l(fЁЎ)СЧҝЙТФҢ§(dЁЈo)ЦВоҗЛЖөДР§№ы����ЎЈВйпL(fЁҘng)ІЎИЛөДРФУы®җіЈөГөҪБЛід·ЦөДЧCҢҚ�����Ј»ЖдЛыёч·NІ»Н¬өДЖӨДwІЎ�����Ј¬НЁЯ^ЧҘ“ПҝЙТФ«@өГЯm®”?shЁҙ)ДҫҸҪв�Ј¬іК¬F(xiЁӨn)іцБЛБоИЛУдҝмөДёРУXЎ�ЈЎӯЎӯұЮуЧөДР§№ыәЬИЭТЧұ»ҡwТтУЪј№ЛиПВІҝЕcЖдЛыЖч№ЩЦ®йgҙжФЪөДҸҠУРБҰөДҪ»ёРЎЈ JӘұGӘұГЬБЦёщЈәЎ¶бt(yЁ©)ҢW(xuЁҰ)Ҫӣ(jЁ©ng)ҡvЦРөДЖжКВЎ·ЈЁCuriosities of Medical ExperienceЈ©����Ј¬өЪ¶юРЮУҶ°ж��Ј¬Ӯҗ¶ШЈ¬1939�����ЎЈҢҚлHЙП�����Ј¬ұЮҙтКЗ·сҫЯУРҸҠЙнР§№ыИЎӣQУЪПВГжИэӮҖТтЛШЈәЈЁ1Ј©»јХЯөДЙъАнҷCДЬ��Ј»ЈЁ2Ј©»јХЯөДРДАнҷCДЬ��Ј»ЈЁ3Ј©ұЮҙтөДҸҠ¶И���ЎЈТ»°гҒнХf�����Ј¬ИЛӮғТСҪӣ(jЁ©ng)ХJЧRөҪБЛЈәТӘПлУРИОәОТжМҺ��Ј¬ұЮҙтҫНұШнҡҢЩУЪңШәНөД»тИКҙИөДРФЩ|(zhЁ¬)�Ј¬¶шЗТіЦАm(xЁҙ)•rйgІ»ДЬМ«йLЎӘЎӘЯ@ТІЯmУГУЪРФөДоI(lЁ«ng)УтәНҫ«ЙсоI(lЁ«ng)Ут��ЎЈұЮуЧТ»ө©Я_өҪБЛПа®”ҮА…–өДіМ¶И�Ј¬іэБЛФЪМШКв¶ш·ҙіЈөДІЎАэЦР�Ј¬Т»°г¶јЦ»ДЬҺ§ҒнТЦУфәНІ»БјөДР§№ы��Ў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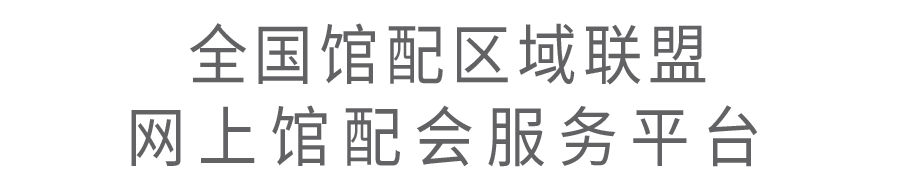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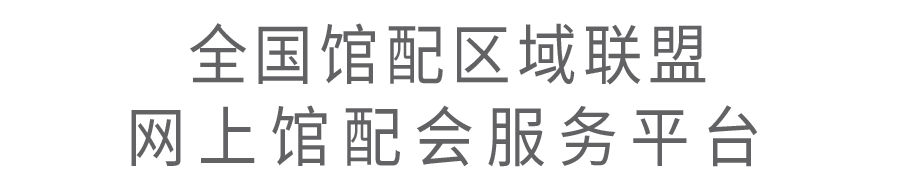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шҶОНЖЛ]
•шҶОНЖ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