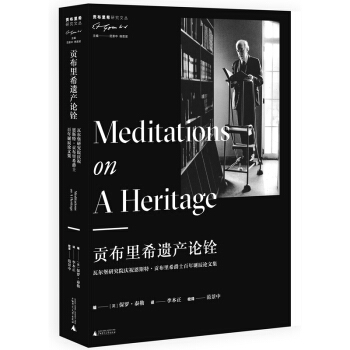ę² čį
▓ķĀ¢╦╣·╗¶Ųš
Č„╦╣╠ž · žĢ▓╝└’ŽŻį┌Įė╩▄║┌Ė±Ā¢¬ä(ji©Żng)Ż█Hegel PrizeŻ▌Ą─č▌šf▐oųąīæĄ└Ż║Ī░╚╦éā┐╔ęįŽ“ę╗╬╗īW(xu©”)š▀▒Ē▀_(d©ó)Ą─ūŅ┤¾Š┤ęŌŻ¼Š═╩ŪšJ(r©©n)šµĄž┐┤┤²╦¹���Ż¼▓╗öÓĄžųžą┬įuār(ji©ż)╦¹Ą─šō╩÷ĘĮŽ“��Ż¼▀@ę╗³c(di©Żn)į§śėųžÅ═(f©┤)ę▓▓╗▀^Ęų���ĪŻĪ▒▒M╣▄┐╔░č▀@┐┤ū„┼·įu╩ĮĄžšä?w©┤)ō╦¹╦∙šJ(r©©n)×ķĄ─║┌Ė±Ā¢Ż█HegelŻ▌ī”├└ąg(sh©┤)╩ĘĄ─žō(f©┤)├µė░Ēæ╦∙ū÷Ą─╬─č┼▐qĮŌ�Ż¼Ą½ę▓╩ŪžĢ▓╝└’ŽŻšJ(r©©n)×ķ▓╗╚▌ĀÄ▐qĄ─╩┬īŹ(sh©¬)ĪŻĄ─┤_�Ż¼╦¹į┌ŲõĪČų╚ą“ĖąĪĘŻ█The Sense of OrderŻ▌Ż©1979─ĻŻ®Ą─ą“čįųą╠ß│÷┴╦ĻP(gu©Īn)ė┌└ŅĖ±Ā¢Ż█RieglŻ▌Ą─═¼śėĄ─šō³c(di©Żn)Ż¼┐╔ęį░č▀@┐┤ū„š┘ķ_▀@┤╬čąėæĢ■Ą─└Ēė╔�Ż¼▒ŠĢ°╦∙ģR╝»Ą─šō╬─Š═╩Ūį┌▀@┤╬čąėæĢ■╔Ž░l(f©Ī)▒ĒĄ─ĪŻ
žĢ▓╝└’ŽŻĻP(gu©Īn)ė┌║┌Ė±Ā¢║═└ŅĖ±Ā¢Ą─čįšōųą╠N(y©┤n)║¼ų°▀@śėĄ─ų„Åł��Ż¼╝┤╦¹éāĻP(gu©Īn)ė┌Üv╩ĘĄ─ė^─Ņ���Ż¼╗“š▀Š═└ŅĖ±Ā¢Č°čį�Ż¼Ė³├„┤_ĄžųĖĻP(gu©Īn)ė┌├└ąg(sh©┤)╩ĘĄ─ė^─Ņ�����Ż¼╩Ū▀Bž×Ą─���ĪóŅHėąė░ĒæĄ─�ĪŻĄ½╩Ū���Ż¼į┌žĢ▓╝└’ŽŻęč│÷░µĄ─öĄ(sh©┤)┴┐²ŗ┤¾Č°ėųČÓĘNČÓśėĄ─ų°ū„ųą����Ż¼ę¬▒µūR│÷ĻP(gu©Īn)ė┌▀@ą®įÆŅ}Ą─ŽÓī”▀Bž×Ą─ę╗ĮMė^─ŅŠ═▓╗─Ū├┤╚▌ęū┴╦�����ĪŻ╦¹į┌╦¹─ŪéĆ(g©©)Ģr(sh©¬)┤·Ą─├└ąg(sh©┤)╩ĘīW(xu©”)╝ęųąōĒėąĘŪĘ▓Ą─Ąž╬╗����Ż¼ę“?y©żn)ķŲõ«É│ŻÅV┤¾Ą─ūxš▀╚║▓╗āH░³└©╦¹Ą─īŻśI(y©©)═¼╚╦Ż¼Č°Ūę░³└©öĄ(sh©┤)┴┐Ė³ČÓĄ─ę╗░Ń╣½▒Ŗ����ĪŻį┌▀@éĆ(g©©)ĘĮ├µŻ¼ė┌1950─Ļ╩ū┤╬│÷░µĄ─ĪČ╦ćąg(sh©┤)Ą─╣╩╩┬ĪĘŻ█The Story of ArtŻ▌╚ĪĄ├Ą─│╔╣”’@╚╗╩Ūų┴ĻP(gu©Īn)ųžę¬Ą─���ĪŻ╦³ų«╦∙ęįŠ▀ėąÅŖ(qi©óng)┴ęĄ─╬³ę²┴”�Ż¼▓╗āHę“?y©żn)ķŲõ’L(f©źng)Ė±├„╬·����Ż¼ęį╝░▓╗ų╗╩Ū░┤─Ļ┤·▀M(j©¼n)ąąĖ┼╩÷����Ż¼Č°Ūęę“?y©żn)ķ╦³░³║¼ų°ę╗éĆ(g©©)ą┬ĘfČ°łėą╚ż╬ČĄ─šō³c(di©Żn)�ĪŻįSČÓūx▀^┤╦Ģ°Ą─╚╦’@╚╗ę▓įĖęŌūx╦¹Ą─Ųõ╦¹ų°ū„Ż¼╔§ų┴ĘŪ│ŻīŻśI(y©©)Ą─ų°ū„�Ż¼ę“?y©żn)ķį┌╦¹Ą─Äū║§╦∙ėąų°╩÷ųąŻ¼╦¹Č╝įO(sh©©)Ę©śŗ(g©░u)Į©ę╗éĆ(g©©)Š▀ėąÅVĘ║║¼┴xĄ─šō³c(di©Żn)���Ż¼ę╗░ŃČ╝╩Ūęįę╗ĘNŪÕ╬·Č°═©╦ūęūČ«Ą─ĘĮ╩ĮüĒ▒Ē▀_(d©ó)Ą─��ĪŻ
╚ńžĢ▓╝└’ŽŻ▒Š╚╦į┌įSČÓł÷║Ž╦∙ĻU├„Ą──Ūśė����Ż¼ĪČ╦ćąg(sh©┤)Ą─╣╩╩┬ĪĘųąĄ─ė^─Ņ┼c║¾üĒĪČ╦ćąg(sh©┤)┼cÕe(cu©░)ėXĪĘŻ█Art and IllusionŻ▌Ż©1960─ĻŻ®ųą╠Į╦„Ą─ę╗ą®ė^─ŅėąĻP(gu©Īn)�����ĪŻĄ½╩Ūį┌═Ē─Ļ���Ż¼╦¹ėąĢr(sh©¬)╦Ų║§░Ą╩Šį┌╦¹Ą─╣żū„ųąėąę╗ĘNĖ³š¹¾wąįĄ─ūhŅ}��ĪŻę“┤╦�����Ż¼į┌╦¹Ų¬Ę∙ūŅķLĄ─ų°ū„ĪČų╚ą“ĖąĪĘĄ─ą“čįųą����Ż¼╦¹╠ߥĮ┴╦ĪČų╚ą“ĖąĪĘ║═╦¹Ė³įńĄ─ų°ū„ĪČ╦ćąg(sh©┤)┼cÕe(cu©░)ėXĪĘĄ─╗źča(b©│)ąį����Ż¼Ī░ę╗ĒŚ(xi©żng)ĻP(gu©Īn)ą─Ą─╩Ūį┘¼F(xi©żn)å¢Ņ}Ż¼┴Ēę╗ĒŚ(xi©żng)ĻP(gu©Īn)ą─Ą─╩Ū╝āįO(sh©©)ėŗ(j©¼)Ī▒���ĪŻ╦¹Įėų°īæĄ└Ż║Ī░╬ꎯ═¹ĪČŽ¾š„Ą─łDŽ±ĪĘŻ█Symbolic ImagesŻ▌Ż©1972─ĻŻ®ę╗Ģ°�����Ż¼ęį╝░╬ę╦∙īæĄ─äeĄ─ĻP(gu©Īn)ė┌öó╩┬╩ųĘ©║═ĮŌßīĘĮĘ©Ą─╬─š┬¼F(xi©żn)į┌┐╔ęį▒╗ęĢ×ķę╗éĆ(g©©)Ė³×ķą█ą─▓¬▓¬Ą─ėŗ(j©¼)äØĄ─ĮM│╔▓┐Ęų��Ż¼▀@ĒŚ(xi©żng)ėŗ(j©¼)äØŠ═╩ŪÅ─ą─└ĒīW(xu©”)ęŌ┴x╔ŽčąŠ┐ęĢėX╦ćąg(sh©┤)Ą─ę╗ą®╗∙▒Š╣”─▄��Ī����ŻĪ▒
┐╝æ]ĄĮ╦¹╦∙░l(f©Ī)▒ĒĄ─Äū║§╦∙ėąĻP(gu©Īn)ė┌öó╩┬┼cšf├„Ż©ģ^(q©▒)äeė┌į┘¼F(xi©żn)Ż®Ą─╬─š┬Č╝ęč╩š╚ļĪČŽ¾š„Ą─łDŽ±ĪĘ�Ż¼╦¹╦∙šfĄ─Ī░╬ę╦∙īæĄ─äeĄ─ĻP(gu©Īn)ė┌öó╩┬╩ųĘ©║═ĮŌßīĘĮĘ©Ą─╬─š┬Ī▒Š┐Š╣╩Ū║╬ęŌ▓ó▓╗ę╗─┐┴╦╚╗��ĪŻĄ½╩Ū�Ż¼1987─Ļ�Ż¼╦¹į┌ę╗Ų¬šäįÆųą╠ß│÷┴╦┼c╦¹Ą─š¹¾węŌłD┤¾ų┬ŽÓ═¼Ą─šō³c(di©Żn)Ż¼ĮŌßī┴╦╦¹×ķ╩▓├┤į┌ĪČ╦ćąg(sh©┤)┼cÕe(cu©░)ėXĪĘų«║¾øQČ©
īóūóęŌ┴”▐D(zhu©Żn)Ž“čb’Ś�����ĪŻ╚ń╦¹╦∙šfŻ║Ī░╬ęĄ─▒¦žō(f©┤)Ī¬Ī¬▀@╩ŪŽÓ«ö(d©Īng)Ė▀╔ąĄ─▒¦žō(f©┤)Ī¬Ī¬╩Ū«ö(d©Īng)ę╗├¹├└ąg(sh©┤)╩ĘĄ─įuūóš▀�ĪŻ╬ꎯ═¹īæę╗Ų¬ī”╦ćąg(sh©┤)░l(f©Ī)š╣ųąīŹ(sh©¬)ļH░l(f©Ī)╔·Ą─╩┬ŪķĄ─įuūóĪŻ╬ęėąĢr(sh©¬)░č╦³┐┤ū„ųąķg╩Ūį┘¼F(xi©żn)�Ż¼ę╗▀ģ╩ŪŽ¾š„Ż¼┴Ēę╗▀ģ╩Ūčb’Ś����ĪŻ╚╦éā┐╔ęįī”╦∙ėą▀@ą®╩┬╬’ū÷ę╗Ę¼╦╝┐╝Ż¼▓óęįĖ³ŠC║ŽĄ─į~Šõšfą®╩▓├┤�ĪŻ╬ęĄ─▒¦žō(f©┤)š²į┌ė┌┤╦Ī��ŻĪ▒
▓╗▀^����Ż¼▀@éĆ(g©©)Ī░ą█ą─▓¬▓¬Ą─ėŗ(j©¼)äØĪ▒╩Ū║╬Ģr(sh©¬)ą╬│╔Ą─Ż┐╦³į┌žĢ▓╝└’ŽŻĄ─╚½▓┐«a(ch©Żn)│÷ųąėąČÓųžę¬Ż┐│§┐┤ŲüĒ�Ż¼╦Ų║§╦¹║▄Š├ęįüĒŠ═ėąę╗éĆ(g©©)╠žČ©Ą─╦╝Žļ╚š│╠Ż¼▓óų▓ĮėĶęį═Ļ│╔����Ż¼Ą½╩ŪŪķør▓óĘŪ╚ń┤╦ĪŻ└²╚ń��Ż¼│÷░µę╗▓┐ĻP(gu©Īn)ė┌łDŽ±ųŠĄ─šō╬─╝»▓ó▓╗╩ŪžĢ▓╝└’ŽŻĄ─ŽļĘ©��Ż¼Č°╩Ū▀~┐╦Ā¢ · ░═┐╦╔ŁĄ┬Ā¢Ą─ų„Åł��Ż¼▀@╩Ū░č╦¹ĻP(gu©Īn)ė┌╬─╦ćÅ═(f©┤)┼dĢr(sh©¬)Ų┌╦ćąg(sh©┤)Ą─ų°╩÷ū÷äØĘųĄ─║Ž└ĒĘĮ╩Į��Ż¼ę“?y©żn)ķ▀@ą®ų°╩÷į┌ę╗▒ŠĢ°ųą╩Ū╚▌╝{▓╗Ž┬Ą─��ĪŻš\╚╗����Ż¼ĪČŽ¾š„Ą─łDŽ±ĪĘ░³║¼įSČÓą┬▓─┴Ž���Ż¼Ųõųąę╗ą®ĘŪ│Żūį╚╗Ąž╔µ╝░ī”Ī░ęĢėX╦ćąg(sh©┤)į┌Ųõą─└ĒīW(xu©”)║¼┴xųąĄ─╗∙▒Š╣”─▄Ī▒Ą─蹊┐�����Ż¼Ą½╩Ū▀@▓óĘŪ▀mė├ė┌╚½Ģ°���ĪŻ
╚╗Č°���Ż¼╝┤╩╣žĢ▓╝└’ŽŻų°ū„Ą─▀Bž×ąį│╠Č╚▓╗╚ń╦¹╦∙┬ĢĘQĄ──ŪśėŻ¼į┌╦¹«ģ╔·╦∙īæĄ─įSČÓų°ū„ųąę▓ėąų°ę╗ž×Ą─ų„Ņ}┼cĘĮĘ©����ĪŻą─└ĒīW(xu©”)╝░Ųõį┌├└ąg(sh©┤)╩ĘųąĄ─æ¬(y©®ng)ė├▒Ē¼F(xi©żn)ūŅ×ķ├„’@ĪŻ▀@éĆ(g©©)šōŅ}╩ŪŠÓžĢ▓╝└’ŽŻĢr(sh©¬)┤·║▄Š├ęįŪ░Ą─ŠSę▓╝{├└ąg(sh©┤)╩ĘĄ─╠ž³c(di©Żn)����Ż¼žĢ▓╝└’ŽŻŪ¾īW(xu©”)Ų┌ķgģó╝ė▀^ą─└ĒīW(xu©”)ųvū∙Ż¼╦¹║¾üĒšfĄ├ęµė┌┐©Ā¢ · ▒╚└šŻ█Karl BühlerŻ▌���ĪŻČ„╦╣╠ž · ┐╦└’╦╣Ż█Ernst KrisŻ▌č¹šł╦¹║Žų°ę╗▒ŠĻP(gu©Īn)ė┌┬■«ŗĄ─Ģ°�����Ż¼ ▀@╩╣╦¹╩▄ĄĮ╣─╬Ķ���Ż¼▒Ż│ų┴╦ī”▀@ę╗ų„Ņ}Ą─┼d╚żĪŻ╚╗Č°��Ż¼╦¹╩▄╣═ė┌═▀Ā¢▒żčąŠ┐į║ų«║¾Ż¼ę¬ł╠(zh©¬)ąąę╗ĒŚ(xi©żng)╚╬äš(w©┤)��Ż¼╝┤š¹└Ē═▀Ā¢▒żĄ─▀zū„Ż█NachlassŻ▌��Ż¼ė╚Ųõ╩ŪĪČłD╝»ĪĘŻ█BilderatlasŻ▌��Ż¼ę“┤╦╦¹▒žĒÜ蹊┐ę╗ą®┼c┤╦Õ─«ÉĄ─å¢Ņ}��ĪŻ
žĢ▓╝└’ŽŻę▓ø]ėą▀xō±╦¹Ą─Ž┬ę╗éĆ(g©©)ĒŚ(xi©żng)─┐�����Ī�����Ż┐╝╠šĀ¢Ą┬蹊┐į║Ż█Courtauld InstituteŻ▌į║ķLč¹šł╦¹┼cŖW═ą · ÄņĀ¢┤─Ż█Otto KurzŻ▌║Žū„�Ż¼×ķ蹊┐į║Ą─īW(xu©”)╔·ū½īæę╗▓┐łDŽ±ųŠĄ─Ė┼šō�����ĪŻ▀@▒ŠĢ°į┌æ(zh©żn)ĀÄŲ┌ķg▒╗öRų├ę╗┼į�����Ż¼ę╗ų▒ø]ėą═Ļ│╔Ż¼Ą½╩Ū╦³Ą─įSČÓ╬─ūų╚įÜł┤µė┌═▀Ā¢▒żčąŠ┐į║Ą─┤“ėĪĖÕųą��ĪŻ║┴¤oę╔å¢�Ż¼į┌ū½īæ┤╦Ģ°Ģr(sh©¬)Ż¼ÄņĀ¢┤─║═žĢ▓╝└’ŽŻų¬Ą└┼╦ųZĘ“╦╣╗∙Ż█PanofskyŻ▌Ą─ĪČłDŽ±īW(xu©”)蹊┐ĪĘŻ█Studies in IconologyŻ▌���Ż¼┤╦Ģ°│÷░µė┌1939─Ļ�����Ż¼═¼─Ļį┌═▀Ā¢▒żłDĢ°^ĄŪėø╚ļāį��ĪŻĄ½╩Ū��Ż¼╦¹éāĄ─蹊┐═ŠÅĮ┼c┼╦ųZĘ“╦╣╗∙į┌ā╔éĆ(g©©)ĘĮ├µ┤¾ŽÓÅĮ═ź�����ĪŻ╩ūŽ╚���Ż¼╦¹éāī”å¢Ņ}łD«ŗŻ█problem picturesŻ▌▓╗╠½Ėą┼d╚żŻ¼Č°▀@ą®łD«ŗ╩Ū┼╦ųZĘ“╦╣╗∙╬─š┬Ą─ų„ę¬Į╣³c(di©Żn)���Ż¼ŽÓĘ┤�����Ż¼╦¹éāīŻūóė┌Š▀Ž¾╦ćąg(sh©┤)Ą─ś╦(bi©Īo)£╩(zh©│n)«ŗĘN┼cų„Ņ}�����ĪŻŲõ┤╬����Ż¼žĢ▓╝└’ŽŻų┴╔┘╩Ū║¼ąŅĄžŻ¼▓╗šJ(r©©n)×ķ┼╦ųZĘ“╦╣╗∙į┌Ųõī¦(d©Żo)šōųąī”Ū░łDŽ±ųŠ├Ķ╩÷Ż©ī”«ŗųąīŹ(sh©¬)ļH▒Ē¼F(xi©żn)ų«╬’Ą─▒µšJ(r©©n)Ż®���ĪółDŽ±ųŠŻ©ī”ų„Ņ}Ą─▒µšJ(r©©n)Ż®║═Ė³╔ŅęŌ┴x╔ŽĄ─łDŽ±ųŠŻ©║¾üĒ▒╗┼╦ųZĘ“╦╣╗∙ĘQ×ķłDŽ±īW(xu©”)�Ż¼╦³╦Ų║§ĻP(gu©Īn)ūóų„Ņ}Ą─┬ō(li©ón)Žļ┼c║¼┴xŻ®ų«ķgĄ─ģ^(q©▒)Ęų╩Ūš²┤_Ą─��ĪŻį┌žĢ▓╝└’Ž��Ż┐┤üĒ���Ż¼Ū░ā╔éĆ(g©©)ĘČ«ĀķgĄ─ģ^(q©▒)Ęų╩Ū╚╦×ķĄ─Ż¼ę“?y©żn)ķį┌įSČÓŪķørŽ┬�Ż¼ī”╦ćąg(sh©┤)╝ę╦∙├Ķ└LĄ─╩┬╬’Ą─▒µšJ(r©©n)▓╗─▄┼cī”ų„Ņ}Ą─▒µšJ(r©©n)ŽÓĘųļxĪŻ
į┌┤╦��Ż¼žĢ▓╝└’ŽŻĄ─Ų³c(di©Żn)Ż¼╚ńį┌╦¹įńŲ┌ĻP(gu©Īn)ė┌┬■«ŗĄ─ų°ū„ųąę╗śė�Ż¼’@╚╗╩Ūų¬ėXą─└ĒīW(xu©”)ĪŻ▀@╦Ų║§╩Ū╦¹īóĻP(gu©Īn)ė┌öó╩┬┼cšf├„Ą─╦╝Žļ┼c╦³éāĄ─ą─└ĒīW(xu©”)║¼┴xŽÓ┬ō(li©ón)ŽĄĄ─ę╗ĘNĘĮ╩Į��ĪŻĄ½╩Ūį┌┬■«ŗ蹊┐ųą�����Ż¼žĢ▓╝└’ŽŻī”╦ćąg(sh©┤)╝ę▓╔ė├┴╦ūāą╬╩ųĘ©Č°╩ņŽż▒╗«ŗš▀Ą─╚╦ģs─▄▒µšJ(r©©n)│÷«ŗĄ─ī”Ž¾Ą─ĘĮ╩ĮĖą┼d╚ż��Ż¼į┌žĢ▓╝└’ŽŻ║═┼╦ųZĘ“╦╣╗∙ī”
łDŽ±ųŠĄ─蹊┐ųą�����Ż¼ā╔╚╦╦∙īæĄ─ų„ę¬╩ŪĻP(gu©Īn)ė┌╦¹éāĄ─═¼Ģr(sh©¬)┤·╚╦�Ż¼ė╚Ųõ╩Ū═¼Ģr(sh©¬)┤·Ą─├└ąg(sh©┤)╩ĘīW(xu©”)╝ęŻ¼▒µšJ(r©©n)│÷═∙╬¶▒╗į┘¼F(xi©żn)ų„Ņ}Ą─Ė„ĘNĘĮ╩Į��Ż¼╝┤╩╣╦¹éāėąĢr(sh©¬)ę▓┐╝æ]▀@ą®ų„Ņ}ī”═∙╬¶Ą─╚╦éāęŌ╬Čų°╩▓├┤���ĪŻ╚╗Č°����Ż¼ĻP(gu©Īn)ė┌ūŅ│§Ą─ė^š▀─▄ʱ▒µšJ(r©©n)│÷ų„Ņ}��Ż¼╠╚╚¶─▄Ż¼ėų╩Ū╚ń║╬▒µšJ(r©©n)Ą─�Ż¼ā╔╬╗ū„š▀Č╝║▄╔┘šä╝░ĪŻžĢ▓╝└’ŽŻšJ(r©©n)×ķ�����Ż¼ę╗Ę∙öó╩┬«ŗ
▒ž╚╗▓╗Ž±ę╗ÅłššŲ¼�Ż¼ę“?y©żn)ķ╦ćąg(sh©┤)╝ę×ķ┴╦ųv╩÷╣╩╩┬Ż¼▓╗Ą├▓╗╩╣ė├Ė„ĘNĘŪūį╚╗ų„┴x╩ųČ╬�ĪŻį┌žĢ▓╝└’ŽŻĄ─▀@ĘNė^³c(di©Żn)ųąŻ¼╬ęéāŽ“▀@éĆ(g©©)å¢Ņ}▀~▀M(j©¼n)┴╦ę╗▓Į�����ĪŻ▀@Š═ęŌ╬Čų°ė^š▀ī”▀@ą®╩ųČ╬Ą─└ĒĮŌ╬┤▒žėą┐╔┐┐Ą─Üv╩Ęę└ō■(j©┤)�ĪŻ
ė╔▀@▓┐Ģ°ĖÕ¼F(xi©żn)┤µĄ─Ų¼Č╬┐╔ęį├„’@┐┤ĄĮŻ¼žĢ▓╝└’ŽŻĄ─ĘĮĘ©▒╚ÄņĀ¢┤─Ą─ĘĮĘ©ę¬ÅVĘ║Ą├ČÓ���Ż¼└²╚ń�Ż¼╦³░³└©ī”Ž¾š„���Īóā║═»╦ćąg(sh©┤)║═įŁ╩╝╦ćąg(sh©┤)Ą─ę╗ą®ėæšōĪŻ▒M╣▄Ģ°ĖÕę╗ų▒ø]ėą═Ļ│╔�Ż¼žĢ▓╝└’ŽŻģs└^└m(x©┤)╦╝┐╝┴╦╦¹į°įćłDį┌Ģ°ĖÕųą╠ĮėæĄ─å¢Ņ}�����Ż¼╔§ų┴į┌Å─╩┬ī”═▀Ā¢▒żė^─ŅĄ─蹊┐Ģr(sh©¬)ę▓╩Ū╚ń┤╦�ĪŻĻP(gu©Īn)ė┌═▀Ā¢▒żĄ─Ģ°ĖÕ┤¾▓┐Ęųīæė┌1946 Ī¬1947─Ļ�����Ż¼Ą½╩Ū�Ż¼ė╔ė┌│¼║§╦¹┐žųŲĄ─ŪķørŻ¼įōĢ°ų▒ų┴1972─Ļ▓┼│÷░µ�����Ż¼▓óį÷╝ė┴╦ę╗ą®é„ėø▓─┴Ž��ĪŻ═¼ę╗Ģr(sh©¬)Ų┌��Ż¼žĢ▓╝└’ŽŻį┌╦¹░l(f©Ī)▒Ēė┌1947─ĻĄ─šō╬─ĪČŽ¾š„Ą─łDŽ±ĪĘŻ█Icones symbolicaeŻ▌ųą╠Į╦„┴╦Ī¬Ī¬ļm╚╗ų╗╩ŪęįėąŽ▐Ą─ĘĮ╩Į╠Į╦„Ī¬Ī¬Ž¾š„ą╬Ž¾Ą─ą─└ĒīW(xu©”)║¼┴x��Ż¼▓óöMČ©┴╦Ņ}×ķĪČłDŽ±Ą─ŅI(l©½ng)ė“║═ĘČć·ĪĘŻ█The Realm and Range of the ImageŻ▌ę╗Ģ°Ą─╠ߊV�ĪŻ╦¹ė┌1947─Ļ║═1952─ĻŽ“│÷░µ╔╠═Ų╦]┤╦Ģ°Ż¼ģs╬┤½@│╔╣”�����ĪŻ┤╦Ģ°Ęų×ķ╚²éĆ(g©©)▓┐ĘųŻ║łDŽ±┼c¼F(xi©żn)īŹ(sh©¬)Ż█Image and RealityŻ▌Īó łDŽ±┼cęŌ┴xŻ█Image and MeaningŻ▌║═łDŽ±┼cą┼č÷Ż█Image and BeliefŻ▌�����ĪŻ«ö(d©Īng)╚╗����Ż¼Ą┌Č■║═Ą┌╚²▓┐Ęų┼c▒╗Ę┼ŚēĄ─łDŽ±ųŠĖ┼šō├▄ŪąŽÓĻP(gu©Īn)Ż¼░³└©ī”┼cłDŽ±ŽÓ┬ō(li©ón)ŽĄĄ─╔±ŲµŽļĘ©│ų└m(x©┤)┤µį┌Ą─┐╝▓ņ�����Ż¼Ą┌ę╗▓┐ĘųätŅA(y©┤)╩Š┴╦īóį┌ĪČ╦ćąg(sh©┤)┼cÕe(cu©░)ėXĪĘųą│÷¼F(xi©żn)Ą─įSČÓų„Ņ}���ĪŻ
ĪČłDŽ±Ą─ŅI(l©½ng)ė“║═ĘČć·ĪĘ╩Ūūį╩╝Š═ė╔žĢ▓╝└’ŽŻ¬Ü(d©▓)┴ó▓▀äØĄ─Ą┌ę╗▒ŠĢ°��Ż¼│²ĪČŲ½É█įŁ╩╝ąįĪĘŻ█The Preference for the PrimitiveŻ▌Ż©2002─ĻŻ®═Ō�����Ż¼ę▓╩Ū╦¹╬©ę╗ę╗▒Š¬Ü(d©▓)┴ó▓▀äØĄ─Ģ°�����ĪŻ▀@éĆ(g©©)ĒŚ(xi©żng)─┐ĘŪ│Ż²ŗ┤¾�Ż¼▓╗ŪąīŹ(sh©¬)ļH����Ż¼▀@ę▓įS╩Ū╦¹╬┤─▄šęĄĮ│÷░µ╔ńĄ─įŁę“ĪŻ╦³╝╚▒Ē├„┴╦╦¹Ą─┼d╚żĘČć·║═¬Ü(d©▓)äō(chu©żng)ąįęį╝░╦╝Žļ▒¦žō(f©┤)��Ż¼ę▓▒Ē├„┴╦╦¹ų°ū„īóĢ■│÷¼F(xi©żn)Ą─╠ž³c(di©Żn)�Ż¼╝┤╬┤─▄šJ(r©©n)ūRĄĮį┌š¹▒ŠĢ°Ą─┬■ķLŲ¬Ę∙ųą▒Ż│ųę╗éĆ(g©©)§r├„Ą─šō³c(di©Żn)ėąČÓ├┤└¦ļyĪŻ╠╚╚¶╚ń┤╦�����Ż¼ė╔╦¹║¾üĒ╦∙īæĄ─ĻP(gu©Īn)ė┌ŅÉ╦ŲšōŅ}Ą─ų°╩÷ųą┐╔ęįŪÕ│■Ąž┐┤ĄĮ����Ż¼╦¹ŽŻ═¹╦¹Ą─ų°ū„ī”ė┌Ųš═©ūxš▀Č°čį£\’@ęūČ«Ż¼═¼Ģr(sh©¬)įćłD╩╣╦¹Ą─šōūCć└(y©ón)ųö(j©½n)Č°╚½├µ�����ĪŻĄ½╩Ū▀@ā╔éĆ(g©©)─┐ś╦(bi©Īo)│Ż│Ż░l(f©Ī)╔·ø_═╗�����ĪŻį┌╦¹ĻP(gu©Īn)ė┌═▀Ā¢▒żĄ─ų°ū„╗“š▀ĪČ╦ćąg(sh©┤)Ą─╣╩╩┬ĪĘųąŻ¼▀@éĆ(g©©)å¢Ņ}▓ó▓╗├„’@�Ż¼┐╔─▄╩Ūę“?y©żn)ķį┌▀@ā╔▒ŠĢ°└’╦¹ČÓ╔┘Ą├▓╔ė├░┤─Ļ┤·Ēśą“┼┼┴ąĄ─ĮY(ji©”)śŗ(g©░u)ĪŻ
æ(zh©żn)ĀÄŲ┌ķg�Ż¼žĢ▓╝└’ŽŻ’@╚╗ŽÓ«ö(d©Īng)├ŃÅŖ(qi©óng)ĄžĮė╩▄┴╦īæū„ĪČ╦ćąg(sh©┤)Ą─╣╩╩┬ĪĘĄ─╬»═ąĪŻ1945─ĻĄū����Ż¼╦¹ū„×ķĖ▀╝ē蹊┐åT╗žĄĮ═▀Ā¢▒żčąŠ┐į║Ż¼└^└m(x©┤)ū½īæĻP(gu©Īn)ė┌═▀Ā¢▒żĄ─ų°ū„���ĪŻ«ö(d©Īng)Ģr(sh©¬)Ą─į║ķLĖź└’┤─ · į·┐╦╦╣?f©żn)¢Ż█Fritz SaxlŻ▌╝▒ŪąĄžŽŻ═¹į┌─Ū▒Š═©╦ūų°ū„ų«Ū░╦¹─▄ā×(y©Łu)Ž╚═Ļ│╔▀@éĆ(g©©)ĒŚ(xi©żng)─┐�����Ż¼▀@╩Ū┐╔ęį└ĒĮŌĄ─�����ĪŻį┌į·┐╦╦╣?f©żn)¢ė?947─Ļ╚ź╩└║¾���Ż¼žĢ▓╝└’ŽŻ│╔×ķę╗├¹ĮK╔Ē┬ÜåTŻ¼▓óė┌1949─Ļ═Ļ│╔┴╦ĪČ╦ćąg(sh©┤)Ą─╣╩╩┬ĪĘĢ°ĖÕ���ĪŻ▀@▒ŠĢ°Š█Į╣ė┌į┌▓╗═¼Ą─Ģr(sh©¬)┤·║═Ąž³c(di©Żn)╚╦éāę¬Ū¾╗“š▀Ų┌┤²╦ćąg(sh©┤)╝ęł╠(zh©¬)ąą▓╗═¼Ą─╚╬äš(w©┤)����Ż¼ęį╝░╦ćąg(sh©┤)╝ę×ķ┴╦ū÷ĄĮ▀@ę╗³c(di©Żn)Č°▓╔ė├╗“š▀░l(f©Ī)├„Ą─╩ųČ╬ĪŻĢ°ųąĄ─šō╩÷╩«Ęų║åå╬��Ż¼▀@į┌║▄┤¾│╠Č╚╔Ž╩Ūė╔ė┌╦³╩ūŽ╚╩Ū×ķŪÓ╔┘─Ļ╦∙īæĄ─���Ż¼▒M╣▄╦³’@╚╗▓╗ų╗ī”ŪÓ╔┘─ĻŠ▀ėą╬³ę²┴”ĪŻ╦³ų„ꬊųŽ▐ė┌į┘¼F(xi©żn)╦ćąg(sh©┤)��Ż¼Ūę▒╚įńŲ┌Ą─ę╗░ŃąįÜv╩ĘŅ}▓─ėą╚żĄ├ČÓ����ĪŻŠ▀¾wĄžšfŻ¼╦³░č▀B└m(x©┤)Ą─╦ćąg(sh©┤)’L(f©źng)Ė±┐┤ū„éĆ(g©©)äe╦ćąg(sh©┤)╝ęī”ą┬Ą─ąĶę¬║═ą┬Ą─Ūķørū÷│÷Ą─Ę┤æ¬(y©®ng)��Ż¼Č°ĘŪīóŲõ┐┤ū„▒Ē¼F(xi©żn)┴╦─│╠žČ©╔ńĢ■Ą─ąį┘|(zh©¼)�Ż¼╗“š▀╚ń╬ųĀ¢Ę“┴ųŻ█WölfflinŻ▌╦∙šfŻ¼▀@╩Ū░┤šš─│ą®ę╗░ŃįŁ└ĒČ°ūā╗»Ą─���ĪŻ
ĪČ╦ćąg(sh©┤)Ą─╣╩╩┬ĪĘĄņČ©┴╦žĢ▓╝└’ŽŻĄ─┬Ģūu(y©┤)����Ż¼Ą½╩Ū╦¹Ą─┼d╚żģs┴Ēėą╦∙į┌���Ż¼ė╔╦¹ŽļĘĮįO(sh©©)Ę©ę¬×ķĪČłDŽ±Ą─ŅI(l©½ng)ė“║═ĘČć·ĪĘšęĄĮę╗╝ę│÷░µ╔ń╝┤┐╔├„’@┐┤ĄĮ▀@ę╗³c(di©Żn)�����ĪŻ╦¹║¾üĒšf�����Ż¼ĪČ╦ćąg(sh©┤)┼cÕe(cu©░)ėXĪĘĪ░┐╔ęį┐┤ū„Ī▒ī”ĪČ╦ćąg(sh©┤)Ą─╣╩╩┬ĪĘĄ─Ī░įuūóĪ▒����Ż¼Ą½īŹ(sh©¬)┘|(zh©¼)╔Ž─Ūų╗╩Ū▒Ē▀_(d©ó)┴╦▀@śėę╗ĘNęŌ╦╝Ī¬Ī¬╦³╩ŪĻP(gu©Īn)ė┌į┘¼F(xi©żn)╦ćąg(sh©┤)Ą─Ż¼▓┐ĘųĄž╠Įėæ┴╦▀@ĘN╦ćąg(sh©┤)×ķ╩▓├┤Ģ■ėąę╗▓┐Üv╩ĘĄ─å¢Ņ}���ĪŻš²╚ń└Ē▓ķĄ┬ · ╬ķĄ┬ĘŲĀ¢Ą┬Ż█Richard WoodfieldŻ▌ūŅĮ³╦∙ųĖ│÷Ą─�����Ż¼║▄ļyÅ─š¹▒ŠĢ°ųą╠ß╚Īę╗éĆ(g©©)▀Bž×Ą─šō³c(di©Żn)���Ż¼ę“?y©żn)ķ▀@▒ŠĢ°Ųį┤ė┌ę╗ŽĄ┴ąųvū∙ĪŻ▓┐Ęųå¢Ņ}į┌ė┌����Ż¼žĢ▓╝└’ŽŻćLįć═¼Ģr(sh©¬)ßśī”ā╔ŅÉūxš▀Ż║─Ūą®╩ņŽżų¬ėXą─└ĒīW(xu©”)Č°ęŌūRĄĮ╦¹╦∙ėæšōå¢Ņ}Å═(f©┤)ļsąįĄ─ūxš▀�Ż¼ęį╝░▓╗Š▀ėą▀@ĘNīŻśI(y©©)ų¬ūRĄ─ÅV┤¾╣½▒Ŗ����ĪŻĄ½╩Ū▀@▒ŠĢ°½@Ą├┬Ģūu(y©┤)╩Ū└Ē╦∙«ö(d©Īng)╚╗Ą─Ż¼╦³╦∙«a(ch©Żn)╔·Ą─ė░Ēæ║▄╚▌ęū└ĒĮŌ��ĪŻį┌įSČÓūxš▀┐┤üĒ�Ż¼╦³ūŅ’@ų°Ą─╠žš„ę╗Č©╩ŪžĢ▓╝└’ŽŻ░čį┌ūŅÅV┴x╔ŽĄ─łD«ŗį┘¼F(xi©żn)«ö(d©Īng)ū„ų„Ņ}Ą─ĘĮ╩ĮŻ¼╝╚▓╗┼┼│Ōę▓▓╗ŠųŽ▐ė┌╬„ĘĮ╦ćąg(sh©┤)Ą─£╩(zh©│n)ät�ĪŻ▀@▒Š╔ĒŠ═īóĪČ╦ćąg(sh©┤)┼cÕe(cu©░)ėXĪĘÅ─╦∙ėąĻP(gu©Īn)ė┌├└ąg(sh©┤)╩ĘĄ─Ģ°╝«ųąģ^(q©▒)Ęųķ_üĒ���Ż¼¤ošō─Ūą®Ģ°╩ŪīæĮoŲš═©ūxš▀Ą─���Ż¼▀Ć╩ŪīæĮoīW(xu©”)š▀ą═ūxš▀Ą─ĪŻ═¼śėę²╚╦ūó─┐Ą─╩Ū�����Ż¼╦¹šJ(r©©n)×ķ╦ćąg(sh©┤)╝ęį┌╚╬║╬Ģr(sh©¬)Ų┌Č╝▓╗ų╗╩Ū║åå╬├Ķ└L╦¹éāų«╦∙ęŖ�Ż¼▓óĮŌßī┴╦╦ćąg(sh©┤)╝ęį┌šŲ╬šį┘¼F(xi©żn)Ą─▀^│╠ųą╦∙įŌė÷Ą─└¦ļyŻ¼▀@ĘNšŲ╬šūŅĮK╩Ūį┌19╩└╝o(j©¼)½@Ą├Ą─���ĪŻ┤╦Ģ°ų«╦∙ęį▓╗═¼Ę▓Ēæ��Ż¼╩Ūę“?y©żn)ķ╦³Å─ą─└ĒīW(xu©”)Ą─ęĢĮŪ�����Ż¼ęįę╗ĘNą┬Ęf�����Īó═©╦ūęūČ«║═ÖÓ(qu©ón)═■Ą─ĘĮ╩ĮĻU├„┴╦╬„ĘĮ╦ćąg(sh©┤)Ą─Üv╩Ę�ĪŻ
žĢ▓╝└’ŽŻį┌ĪČų╚ą“ĖąĪĘĄ─ą“čįųąĮŌßīŻ¼╦¹į┌═»─ĻĢr(sh©¬)Š═ęčī” ornamentŻ█╝y’ŚŻ▌║═ decorationŻ█čb’ŚŻ▌Ėą┼d╚ż���Ż¼Ą½╩Ū����Ż¼ų▒ĄĮĪČ╦ćąg(sh©┤)┼cÕe(cu©░)ėXĪĘå¢╩└�Ż¼╦¹Č╝ø]ėąŽļĄĮ▀^ę¬╔Ņ╚ļ蹊┐▀@ę╗šōŅ}Ż¼Č°┤╦Ģ°Ą─╦„ę²ęÓ▓ó╬┤╠ß╝░čb’Ś���ĪŻ░┤╦¹╦∙╩÷����Ż¼ļSų°Ė„ĘNĖ„śėĄ─ųvū∙č¹šłĄĮüĒ���Ż¼▀@ĘNŽļĘ©ųØuą╬│╔�����ĪŻę“┤╦����Ż¼──┼┬╩Ūį┌╦¹╦∙īæ▀^Ą─ūŅķLŲ¬Ą─ų°ū„ųąŻ¼žĢ▓╝└’ŽŻę▓╦Ų║§╬┤į°═Ļ│╔▀^ę╗éĆ(g©©)ĻP(gu©Īn)ė┌╦ćąg(sh©┤)┼cą─└ĒīW(xu©”)Ą─ķLŲ┌ĒŚ(xi©żng)─┐����ĪŻ╚╗Č°Ż¼╦ćąg(sh©┤)┼cą─└ĒīW(xu©”)ų«ķgĄ─ĻP(gu©Īn)ŽĄ╩Ū╦¹ę╗╔·ųą┤¾▓┐ĘųĢr(sh©¬)ķgĄ─║╦ą─┼d╚ż��Ż¼▀@╩Ū╬Ńė╣ų├ę╔Ą─�Ż¼▀@╩Ūž×┤®╦¹Ą─īW(xu©”)ąg(sh©┤)╗ŅäėĄ─╝tŠĆ���ĪŻ
╚ńĪČ╦ćąg(sh©┤)┼cÕe(cu©░)ėXĪĘę╗śė����Ż¼ĪČų╚ą“ĖąĪĘÅ─ųvū∙Ą─ą╬╩ĮŽ“ę╗▒ŠĢ°Ą─▀^Č╔▓ó▓╗═Ļ╚½│╔╣”��Ż¼ę“?y©żn)ķžĢ▓╝└’ŽŻ╦Ų║§ę╗ų▒įćłD═¼Ģr(sh©¬)ū÷Äū╝■▓╗═¼Ą─╩┬ŪķŻ║╠ß╣®╚╦éāī”┤²čb’ŚŻ█decorationŻ▌æB(t©żi)Č╚Ą─Üv╩ĘĖ┼╩÷�Ż¼╠ß╣®ī”ĘNĘNą╬╩ĮĄ─ęĢėXčb’ŚŻ█visual decorationŻ▌┐ń╬─╗»┴„ąąĄ─ą─└ĒīW(xu©”)ĮŌßī���Ż¼ęį╝░ėæšōĻP(gu©Īn)ė┌čbŻ█ornamentŻ▌Ą─╩╣ė├┼c░l(f©Ī)š╣Ą─įSČÓÕ─╚╗▓╗═¼Ą─å¢Ņ}Ż¼¤ošōį┌Į©ų■ųą���ĪóĘ■čbųą�Ż¼▀Ć╩Ū╝yš┬ųą�ĪŻę“┤╦Ż¼ūxš▀ī”ūį╝║▒╗ę²═∙║╬ĘĮęį╝░×ķ╩▓├┤▒╗ę²Ž“─ŪéĆ(g©©)ĄžĘĮ│Ż│ŻĖąĄĮ└¦╗¾���ĪŻ▀@ĘNĢ°ĖÕąĶę¬ę╗╬╗ėąų„ęŖĄ─ŠÄ▌ŗ����Ż¼Ą½╩Ū▒M╣▄╚ń┤╦�Ż¼╦³╚į╚╗▒╚═¼Ģr(sh©¬)Ų┌Äū║§╦∙ėąėó╬─├└ąg(sh©┤)╩ĘĢ°╝«Č╝Ė³╝ėÅV▓®Īóą┬ĘfČ°╚ż╬Č░╗╚╗����ĪŻ
žĢ▓╝└’ŽŻĄ─ūŅ║¾ę╗▒Šų°ū„ĪČŲ½É█įŁ╩╝ąįĪĘŻ¼ę▓╩Ūė╔Ė„ĘNųvū∙ā╚(n©©i)╚▌░l(f©Ī)š╣Č°üĒĄ─���Ż¼▀@ą®ā╚(n©©i)╚▌┤¾Č╝░l(f©Ī)▒Ēė┌┤╦Ģ°│÷░µĄ─Äū╩«─ĻŪ░���ĪŻ┤╦Ģ°Ą─Üv╩Ęöó╩┬╔§ų┴▒╚ĪČų╚ą“ĖąĪĘĖ³ūóųžęįįŁäō(chu©żng)ąį蹊┐×ķ╗∙ĄA(ch©│)��Ż¼Ą½╩Ū����Ż¼Ģ°ųąę▓ėąī”ė┌ą─└ĒīW(xu©”)å¢Ņ}Ą─ę╗Ę¼ėæšō��Ż¼╦³║▄ļy┼cŲõėÓ▓┐ĘųŽÓĘ¹║Ž�����ĪŻį┌▀@Ę¼ėæšōųą���Ż¼žĢ▓╝└’ŽŻ░l(f©Ī)š╣┴╦ęčį┌
ĪČ╦ćąg(sh©┤)┼cÕe(cu©░)ėXĪĘųą┐╝▓ņĄ─ė^─Ņ��Ż¼▓óį┌ę╗ą®ĄžĘĮū÷┴╦ą▐Ė─�����ĪŻĄĮ─┐Ū░×ķų╣Ż¼ĪČŲ½É█įŁ╩╝ąįĪĘĄ─ė░Ēæ▀ĆŽÓ«ö(d©Īng)ėąŽ▐��Ż¼▓┐ĘųįŁę“╩Ū�Ż¼╦³╦∙╠ĮėæĄ─╩Ū╚ż╬Č╩ĘĄ─ę╗éĆ(g©©)ĘĮ├µŻ¼ĻP(gu©Īn)ė┌▀@éĆ(g©©)ĘĮ├µęčėą┤¾┴┐īW(xu©”)ąg(sh©┤)╬─½I(xi©żn)�����ĪŻ▓╗▀^Ż¼╚ń╦¹Ž╚Ū░─Ū▒Šų°ū„ę╗śė�����Ż¼╦³š╣╩Š┴╦žĢ▓╝└’ŽŻī”ė┌Ė„ĘNŅÉą═║═üĒūįĖ„éĆ(g©©)Ģr(sh©¬)Ų┌Ą─╦ćąg(sh©┤)ū„ŲĘĄ─£Y▓®ų¬ūR���Ż¼ęį╝░╦¹ī”═∙╬¶ÜWų▐╩ĘīW(xu©”)╝ę║═┼·įu╝ęų°ū„Ą─╔Ņų¬╩ņ’■�����ĪŻ
╚╦éāŲš▒ķŽÓą┼�Ż¼žĢ▓╝└’ŽŻī”ęŌ┤¾└¹╬─╦ćÅ═(f©┤)┼dĢr(sh©¬)Ų┌Ą─╦ćąg(sh©┤)ėąų°╠žČ©Ą─īŻķL╗“Ų½É█�Ż¼▀@¤oę╔╩ŪÕe(cu©░)š`Ą─ĪŻ╦¹░l(f©Ī)▒Ē┴╦┤¾┴┐ĻP(gu©Īn)ė┌─Ūę╗Ģr(sh©¬)Ų┌Ą─ų°ū„�����Ż¼░³└©ÄūŲ¬śOŠ▀ė░Ēæ┴”Ą─šō╬─�����Ż¼Ą½▀@┼cŲõšfę“?y©żn)ķ╦¹ī”▀@ę╗šōŅ}▒Ż│ųų°╠žäeĄ─┼d╚żŻ¼▓╗╚ńšfę“?y©żn)ķ╦³╩Ū╦¹į┌═▀Ā¢▒żčąŠ┐į║Į╠īW(xu©”)╗ŅäėųąūŅųžę¬Ą─ĮM│╔▓┐Ęų���ĪŻį┌▀xō±ū½īæĻP(gu©Īn)ė┌┘Øų·�����ĪółDŽ±ųŠ�Īó╚ż╬Č╗“š▀╦ćąg(sh©┤)┼·įuĄ─šō╬─Ģr(sh©¬)�����Ż¼╦¹ļy├Ō│Ż│ŻÅ─╬─╦ćÅ═(f©┤)┼dĢr(sh©¬)Ų┌▀x ╚ĪīŹ(sh©¬)└²�ĪŻ╦¹ī”╚RŖW╝{Ā¢ČÓŻ█LeonardoŻ▌╦∙ū÷Ą─įSČÓ蹊┐┐ŽČ©▓╗āHę“?y©żn)ķī”▀@╬╗╦ćąg(sh©┤)╝ę╠žäe┘Ø┘pŻ¼ę▓╚ĪøQė┌▀@śėę╗éĆ(g©©)╩┬īŹ(sh©¬)��Ż¼╝┤╚RŖW╝{Ā¢ČÓėąėø▌dĄ─ĻP(gu©Īn)ė┌└L«ŗĄ─įušō║═╦¹Ą─╦ž├Ķ▀z«a(ch©Żn)«É│ŻžSĖ╗�����Ż¼╝┤╩╣┼c║¾üĒĄ─«ŗ╝ęŽÓ▒╚ę▓╩Ū╚ń┤╦����ĪŻ
žĢ▓╝└’ŽŻį┌īæ╬─š┬Īóįušō╗“š▀ū÷å╬ę╗Ą─ųvū∙Ģr(sh©¬)’@╚╗ūŅ×ķ▌p╦╔ūį╚ń����Ż¼╦¹ęč│÷░µĄ─ų°ū„┤¾▓┐Ęųæ¬(y©®ng)Üw╚ļ▀@ą®ĘČ«ĀĪŻ╚╗Č°�����Ż¼╦¹╗∙▒Š▒▄├Ō╗“š▀═Ļ╚½▒▄├Ō┴╦ā╔ĘNų„ꬥ─├└ąg(sh©┤)╩Ęīæū„ŅÉą═Ż║Ķb┘p║═░l(f©Ī)▒Ēą┬Ą─Üv╩Ę▓─┴Ž���ĪŻŽÓĘ┤����Ż¼╦¹ĖČ│÷Š▐┤¾Ą─┼¼┴”üĒ┼·įuę╗ą®Ųš▒ķĄ─├└ąg(sh©┤)╩Ę蹊┐ĘĮĘ©�Ż¼▀@ĘN┼·įuėąĢr(sh©¬)╩Ū├„┤_Ą─Ż¼Ą½═©│Ż╩Ū║¼
ąŅĄ─��ĪŻ«ö(d©Īng)╚╗����Ż¼Ųõųąų„ę¬ė^─Ņ╩Ū╦ćąg(sh©┤)Ę┤ė│Ģr(sh©¬)┤·Š½╔±Ż¼╦¹īóŲõÜwŅÉ×ķ║┌Ė±Ā¢ų„┴x����ĪŻ╦¹╦∙ėąĻP(gu©Īn)ė┌’L(f©źng)Ė±┼cĢr(sh©¬)╔ąūā▀wĄ─ų°ū„Č╝┐╔┐┤ū„┼c▀@éĆ(g©©)å¢Ņ}ėąĻP(gu©Īn)ĪŻ═¼śėųžę¬Ą─╩Ū��Ż¼╦¹ī”į┌20╩└╝o(j©¼)ųą╚~│ŻęŖĄ──ŪĘNÅ═(f©┤)ļsĄ─łDŽ±ųŠ═ŲöÓ╠ß│÷┴╦┼·įuĪŻ
ļSų°├└ąg(sh©┤)╩Ę░l(f©Ī)š╣�Ż¼žĢ▓╝└’ŽŻģó┼cĄ─įSČÓæ(zh©żn)ČĘę“ęč╚ĪĄ├ä┘└¹Č°╦Ų║§▓╗į┘ėą╩▓├┤ęŌ┴xŻ¼ę“┤╦╦¹╦∙ū½īæĄ─ĻP(gu©Īn)ė┌▀@ą®šōŅ}Ą─ų°ū„ėąįSČÓ▓╗┐╔▒▄├ŌĄž╩¦╚ź┴╦╬³ę²┴”��ĪŻĄ½╩Ū▓╗ę¬═³ėø����Ż¼į┌╦¹ū½īæ▀@ą®ų°ū„Ą─Ģr(sh©¬)║“Ż¼╦¹╦∙Ę┤ī”Ą──Ūą®ė^─Ņ╚į╚╗ī”įSČÓ├└ąg(sh©┤)╩ĘīW(xu©”)╝ę«a(ch©Żn)╔·ÅŖ(qi©óng)┤¾Ą─ė░Ēæ����ĪŻų„ę¬╩ŪųvĄ┬šZĄ─├└ąg(sh©┤)╩ĘīW(xu©”)╝ęŻ¼╦¹éāī”├└
ąg(sh©┤)╩ĘīW(xu©”)┐ŲÅŖ(qi©óng)╝ė┴╦─│ĘN░³┴_╚fŽ¾Ą─¾wŽĄ��Ż¼▓ó┼¼┴”į┌╦ćąg(sh©┤)Ą─Ė„ĘNūā╗»ųą░l(f©Ī)¼F(xi©żn)─│ĘN▒ž╚╗ąį�����Ż¼▀@ĘNū÷Ę©╚į╚╗╩▄ĄĮ╚╦éāę▓įS╩Ū▀^ĘųĄ─ūųž�����ĪŻ═¼Ģr(sh©¬)���Ż¼╦ćąg(sh©┤)ĶbČ©ŽĒėąŠ▐┤¾Ą½╬┤▒ž║Ž║§Ūķ└ĒĄ─┬Ģ═¹���Ż¼įSČÓĻP(gu©Īn)ė┌Š▀¾wū„ŲĘĄ─ų°╩÷░³║¼┴╦ę╗ĘN▓╗Ģ■┴Ņ╬ųĀ¢╠ž · ┼Õ╠žŻ█Walter PaterŻ▌ĖąĄĮ¾@ėĀĄ─įušōĶb┘p����ĪŻ┼cįSČÓ├└ąg(sh©┤)╩ĘīW(xu©”)╝ę▓╗═¼��Ż¼žĢ▓╝└’ŽŻ▓ó▓╗ą¹ĘQ╦¹ī”═∙╬¶╦ćąg(sh©┤)ū„ŲĘĄ─Ę┤æ¬(y©®ng)Š▀ėą╚╬║╬╠žäeĄ─ÖÓ(qu©ón)═■ąį����ĪŻŽÓĘ┤�����Ż¼╦¹│ąšJ(r©©n)�Ż¼└ĒĮŌūŅ│§Ą─ė^▒Ŗī”ė┌▀@ą®ū„ŲĘĄ─Ę┤æ¬(y©®ng)Ż¼╩Ūę╗ĘN║Ž└ĒĄ─Üv╩Ę╠¶æ(zh©żn)�Ż¼╦¹ī”▀@ę╗å¢Ņ}Ą─蹊┐ū÷│÷Ą─žĢ½I(xi©żn)Ī¬Ī¬▀@éĆ(g©©)å¢Ņ}į┌╦¹┬ÜśI(y©©)╔·č─Ą─║¾Ų┌įĮüĒįĮš╝ō■(j©┤)╦¹Ą─ą─ņ`Ī¬Ī¬║▄┐╔─▄Š▀ėą│ųŠ├Ą─ųžę¬ąįĪŻ
ī”ė┌Ųõ├¹ūųĖĮī┘ė┌ę╗ĘN╠žČ©Ą─ĘĮĘ©╗“š▀└ĒšōĄ─Ū░▌ģ���Ż¼├└ąg(sh©┤)╩ĘīW(xu©”)╝ę│Ż│Żęįę╗ĘNę▓įS╩Ū▀^ĘųĄ─│ńŠ┤æB(t©żi)Č╚üĒ┐┤┤²����Ż¼─¬└ū└¹Ż█MorelliŻ▌����Īó╬ųĀ¢Ę“┴ų║══▀Ā¢▒żŻ█WarburgŻ▌Š═╩Ū├„’@Ą─└²ūė����ĪŻžĢ▓╝└’ŽŻ╬┤▒žĢ■╚ĪĄ├▀@ĘNĄž╬╗���Ż¼╗“š▀╬┤▒žĢ■ŽŻ═¹╚ĪĄ├▀@ĘNĄž╬╗����ĪŻ╦¹ĻP(gu©Īn)ė┌╚ż╬Č╩Ęų°ū„Ą─ųžę¬ąį▀Ćėą┤²╚╦éā│õĘųĄžšJ(r©©n)ūR�Ż¼Ą½╩Ū╦¹ūŅėąė░ĒæĄ─žĢ½I(xi©żn)Ż¼▀^╚ź╩Ū�����Ż¼¼F(xi©żn)į┌║▄┐╔─▄╚į╚╗╩Ū�����Ż¼īóą─└ĒīW(xu©”)Ą─░l(f©Ī)š╣æ¬(y©®ng)ė├ė┌ęĢėX╦ćąg(sh©┤)�����ĪŻ╦¹ū÷│÷▀@ę╗žĢ½I(xi©żn)����Ż¼╩Ūę“?y©żn)ķ╦¹▓╗▐oą┴ä┌Ąž┴╦ĮŌęĢėX╦ćąg(sh©┤)ų«═ŌĄ─┴Ēę╗éĆ(g©©)īW(xu©”)┐Ų����ĪŻ╦¹Ą─ĘĮĘ©Ż©▓╗═¼ė┌╦¹Ą─’L(f©źng)Ė±Ż®ø]ėą╩▓├┤¬Ü(d©▓)╠žų«╠Ä�����Ż¼╦¹¤oę╔šJ(r©©n)×ķūį╝║Ą─ĮY(ji©”)šō╩ŪĢ║Ģr(sh©¬)ąįĄ─��ĪŻ╚╗Č°���Ż¼╝┤╩╣─Ūą®ĮY(ji©”)šō▒╗╚Ī┤·Ż¼╗“š▀«ö(d©Īng)╦³éā▒╗╚Ī┤·Ģr(sh©¬)�Ż¼╦¹Ą─įSČÓų°ū„Ż¼ė╔ė┌Ųõ▓╗═¼īż│ŻĄ─ĘČć·��Īóā╚(n©©i)į┌Ą─╚ż╬Čęį╝░ŪÕ╬·Ą─ĻU╩÷��Ż¼ę▓¤oę╔Ģ■└^└m(x©┤)×ķ╚╦éā╦∙ķåūx����Ī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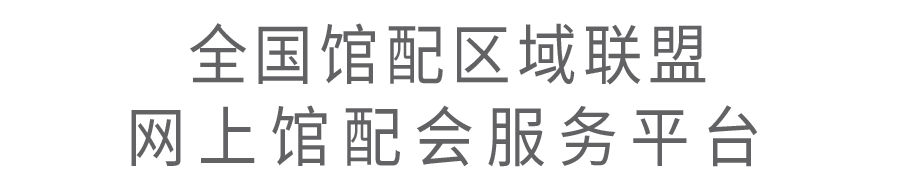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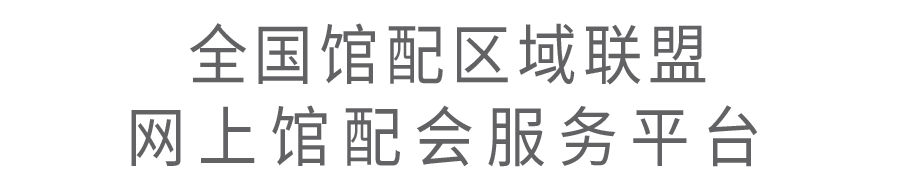


 Ģ°å╬═Ų╦]
Ģ°å╬═Ų╦]